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柳條湖事件”和“盧溝橋事變”,是抗日戰爭兩個重要節點。
柳條湖事件發生在1931年的沈陽東郊,也叫“九一八”事變,東北從此逐步淪為偽滿洲;而盧溝橋事變發生在1937年的盧溝橋,也叫“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兩次事件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
都是日軍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都是“不抵抗主義”的惡果,都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荒于備戰的必然結局,都是坐擁絕對優勢兵力卻以失敗而告終,都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破產的開始。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真實的放大鏡。回顧“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很多人都會有一個大大的疑問:同樣是面對日軍的挑釁和侵略,為什么東北軍不戰而退、29軍卻能奮起抵抗?

日軍駐屯軍司令部天津海光寺
無論是“九一八事變”還是“七七事變”,日軍都是蓄謀已久。
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扶桑國的文明開化還是得益于隋唐時的互通交流。武漢疫情期間,日本的援贈物品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就出自唐代詩人王昌齡之手。
但是,從唐代開始東瀛屢屢以武力侵擾,都以慘敗告終,如唐代白江口之戰,元代有元日之戰,明代抗倭之戰和萬歷朝鮮戰爭。但是,近代甲午戰爭,清廷一敗涂地并簽訂了《馬關條約》。
隨后日俄戰爭,日軍進一步鞏固了在東北的勢力范圍,并開始駐兵。
“九一八事變”前,“皇姑屯事件”讓強硬的張作霖一命嗚呼,“中東路事件”讓少帥張學良被蘇軍打出了陰影。
中原大戰張學良支持蔣氏讓馮、閻、李聯軍落敗,隨后“東北易幟”實現“大一統”,但張學良和“大哥”蔣氏貌合神離,導致日軍在“柳條湖”有恃無恐。
“七七事變”前形勢相似,宋哲元、蔣氏也都是各懷心事,同床異夢。
當時,宋哲元29軍駐守察哈爾、熱河、北平、天津,是日軍進入華北的必經之地。而宋哲元29軍有8萬之眾,附近東北軍、晉綏軍也有15萬人。而日軍有1.4萬人,還有4萬余人偽警察部隊。

1937年7月8日,宛平城守軍增援盧溝橋
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北大營8000人擋不住日軍700人,16.5萬大軍更是被2萬余日軍嚇跑,最終丟掉了爹娘和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張學良敢于背負國人罵名“不抵抗”,有幾個原因:
第一,日軍蓄謀已久,“柳條湖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中國通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此二人都是張氏父子的座上客,而后來導演“盧溝橋事變”,是另一位高級特工土肥原賢二。
第二,日軍的兵力、素質、裝備和技戰術水平,在當時屬于世界一流,而為了鄰居的物產資源覬覦已久的這次戰爭籌備已久,無論是輿論、兵員、物質、情報和作戰方案都可謂細致入微。
第三,武器裝備和兵員素質在國內領先的東北軍,和日軍根本不在一個檔次。別看東北軍和前身奉軍在國內軍閥混戰中耀武揚威,但是一旦和蘇軍接觸立馬崩盤,再和日軍交鋒勝負完全可以預料。
第四,面對日軍的“步步蠶食”,東北軍上下有不少將士是有抵抗意愿的,但是張少帥的“大哥”蔣氏一向善于“借刀殺人”,對日軍可能的入侵態度曖昧,讓東北軍對抵抗日軍心里沒底。
第五,少帥雖然有“家仇國恨”,但畢竟只是一個29歲的二代子弟,雖然繼承了乃父的家業和軍隊,卻無法傳承其父“笑傲江湖”的雄心、野心、手段和霸氣,如此一來不戰而退就是唯一的選擇。

同樣坐擁天時、地利和絕對優勢兵力,宋哲元的29軍敢于反擊,既有當時日軍鐵蹄一旦踏入就有整個華北、甚至整個中國陷入危亡的嚴峻形勢,也有29軍“寧可抗日死,不做亡國奴”的血性。
第一,與武器精良的東北軍在“中東路事件”被蘇軍揍得滿地找牙相比,第29軍在此前兩年的“長城抗戰”因為“喜峰口大刀隊”留下了赫赫威名,打出信心的同時也大漲了國人的志氣。
第二,第29軍上下血性十足,如軍長宋哲元,副軍長佟麟閣;37師師長馮治安,110旅旅長何基灃、219團團長吉星文、3營營長金振中;38師師長張自忠,132師師長趙登禹等等。
第三,七七事變初期,宋哲元、秦德純、張自忠的“和談”幻想,被日軍的全面進攻而粉碎。失去退路的第29軍背水一戰,激發了巨大的愛國熱忱和戰斗精神,讓日軍4天就更換了最高指揮官。
第四,九一八時,北大營官兵也有反抗但被參謀長榮臻制止。盧溝橋金振中3營一開始就得到了宋哲元回授權的最高指揮官、37師師長馮治安默許,而旅長何基灃、團長吉星文都是堅定的主戰派。
第五,七七事變之前,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氏被迫同意了“聯合抗戰”。而第29軍受到攻擊后南京也沒有了退路,不但對29軍派出援兵,隨后還同意了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方案。

不可否認,29軍的盧溝橋抗戰給國人帶來了巨大鼓舞,也堅定了南京和延安團結抗戰的決心。但是,從最終的純軍事結果來看,英勇奮戰的第29軍依然以戰敗撤退而告終。
為什么29軍8萬大軍抵擋1.4萬日軍的進攻,反而落了下風?
究其原因,既有宋哲元、秦德純、張自忠等人抱有“和平相處”的幻想,最終被日軍的“緩兵之計”和出爾反爾所欺騙;也因為8萬大軍只有219團不足4000人備戰,余部幾乎淪為“保安隊”;還有第29軍自“長城抗戰”短短4年就蛻化成李自成的“大順軍”。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國家積貧積弱,難以給29軍挺起寬厚的胸膛。
“七七事變”,7月7日從盧溝橋開始,9日開始打打談談,小的戰斗不斷。
7月17日,蔣氏發表《廬山講話》。7月28日,第29軍的軍部遭到日軍圍攻,隨后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相繼戰死,第29軍前后堅持抵抗月余,后來在南京命令下撤出戰斗轉移戰場。
第29軍將士的浴血奮戰,卻沒有換來“驅逐韃虜”的結果,多少令人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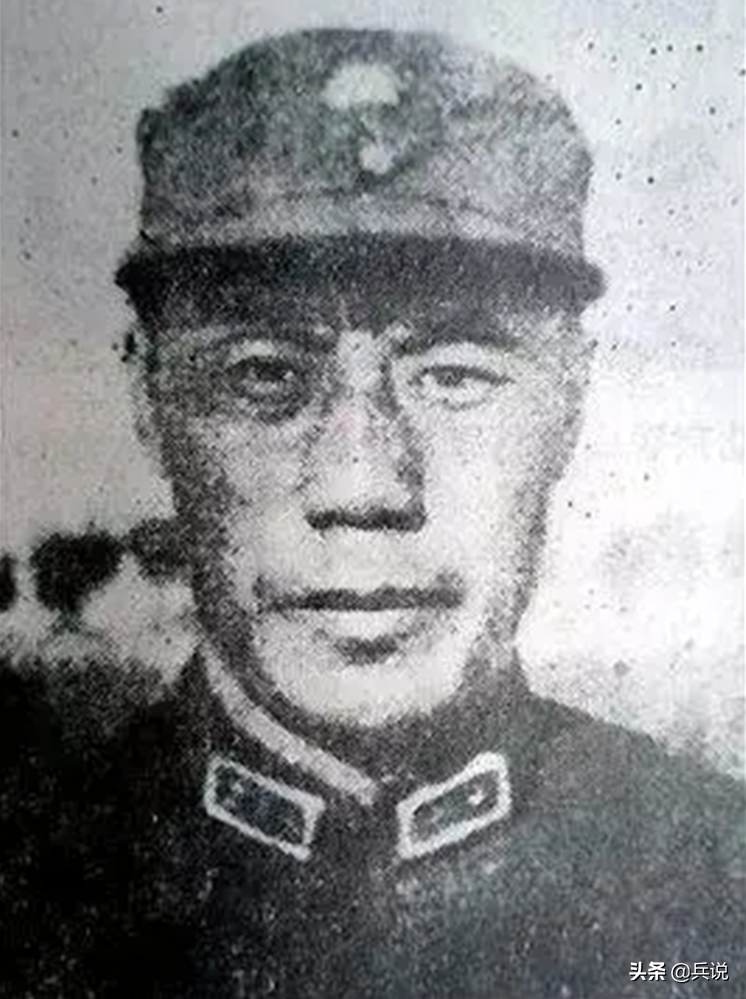
全面抗戰犧牲的第一位副軍長佟麟閣
回顧盧溝橋事變,有幾點刻骨銘心的經驗教訓值得后人銘記:
第一點,和虎視眈眈的日軍搞所謂“和談”與“和平相處”,無異于與虎謀皮,其結果必然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最終落得一個“農夫與蛇”的下場,因為蛇咬農夫是必然的,唯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才是王道。
第二點,無論是一支軍隊,還是一個國家,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告誡都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一旦像二戰開進巴黎的德軍、二戰勝利后進駐東京的美軍一樣,只會玩物喪志失去戰力。
第三點,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明末詩人曹學佺這句名聯,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一支軍隊要保證持久的戰斗力,就要堅持“官兵平等”的良性制度,杜絕等級森嚴、利益分化帶來的腐敗。

第四點,只有融入我軍的大熔爐,第29軍才得到了涅槃和新生。打響全面抗戰第一槍的29軍經歷了曲折坎坷,最終由“臥底將軍”何基灃和張克俠率領在賈汪起義,吹響了淮海戰役的號角。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高悅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