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是什么意思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道德倫理傳統(tǒng)。由于這一文化傳統(tǒng)的浸潤、滋養(yǎng),武術(shù)在蜿蜒的歷史發(fā)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文化內(nèi)容——武德。所謂武德,是指在中國道德倫理文化長期影響下,被習(xí)武群體所自覺認(rèn)同的有關(guān)傳武、習(xí)武、用武的行為規(guī)范。武德的形成與發(fā)展歷經(jīng)了一如流水的漫長歲月,在先秦到清代這段悠悠歲月中,武德大致經(jīng)過了萌芽、豐富與充實(shí)三個階段。

人類文明的初始,不管是為了獲取生活資料的人與獸斗,還是為了贏得各種利益的人與人斗,都留下了“武”的活動印記。尤其是到了國家形式出現(xiàn)后,作為武力的軍事更成為國家的大事。然而,在中華文明史上,武與德很早就結(jié)緣相伴,《左傳·宣公十二年》上所記楚莊王的“止戈為武”四字,或多或少反映出一種對于“武”的道德制約觀念已開始氤氳萌芽,以致稍后正式提出了“武德”這一概念。不過,先秦時期所謂的“武德”,是指軍功而言,并非后來武術(shù)文化語境中的“武德”概念。真正具有武術(shù)文化意味上的一種對習(xí)武者的道德要求,較早見于《史記·太史公自序》。西漢著名史學(xué)家司馬遷在其“自序”中清楚寫道:“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nèi)可以治身,外可以應(yīng)變,君子比德焉。”

司馬遷提出的傳兵論劍者應(yīng)具備的“信、廉、仁、勇”這類道德要求,其時間是在西漢,但作為一種社會實(shí)踐與行為規(guī)范,早在此前已見端倪。如《禮記》中明文規(guī)定:凡是在給人遞交兵械時,一定要注意不能把帶有刃口的一面朝向?qū)Ψ剑允咀鹬亍A硗猓抉R遷還在《史記·游俠列》傳中歸納了有關(guān)“俠”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幾個特點(diǎn),某種意義上也從一個側(cè)面映現(xiàn)出早期武德的一些基本內(nèi)容。

自宋元以后,隨著古代武術(shù)文化的日益成熟,有關(guān)武德的內(nèi)容也逐步豐富起來。大概在五代末宋代初,有位名叫“調(diào)露子”的人編撰了一本《角力記》的書。該書的第一篇“述旨”中開宗明義寫道:兩兩相當(dāng)?shù)慕橇Γ琼椂分嵌酚碌幕顒樱苁谷嗽鎏碛職猓瑥?qiáng)健體魄,敢于斗敵,乃至捐軀沙場,顯然其中包含了“勇能達(dá)德”的內(nèi)容,這也應(yīng)是司馬遷“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有宋一代,武德的最集中閃現(xiàn),是民族英雄岳飛等人的精忠報國,他那“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脊梁,感召了歷代的武林人士。

明清兩代,武德的內(nèi)容得到進(jìn)一步充實(shí),盡管當(dāng)時的文獻(xiàn)中并未明確提出“武德”一詞,但許多文獻(xiàn)資料都不同程度記有這方面內(nèi)容,如明代《峨眉槍法》中的“談玄授道,貴乎擇人”,又如明清之際浙東內(nèi)家拳中的“五不可傳”,再如乾隆七年(1742年)梅花拳傳人楊炳在《習(xí)武序》中訂立的“習(xí)武規(guī)矩十二條”,以及清末《少林拳術(shù)秘訣》中記述的“少林戒約”等。總體上,此時期的武德大致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關(guān)于“師”的要求
如著名軍事家戚繼光在《練兵雜記》一書中提出了“師道”概念,認(rèn)為如果習(xí)武中“師道”得不到確立,則教師所說的話就沒有信譽(yù),對習(xí)練者進(jìn)行的種種訓(xùn)練就沒有人聽從,師道尊嚴(yán)也因此就蕩然無存;同時,對于那些掌握了一種技藝,便視為至寶,不肯隨便教人,而是變著法子索取供養(yǎng),依照收取的財物多少傳授技藝的唯利是圖現(xiàn)象進(jìn)行了批評。

關(guān)于傳人的要求
如明人程真如的《峨眉槍法》中明確提出了“不知者不與言,不仁者不與傳”的擇人要求,稍后浙東內(nèi)家拳則立有“心險者,好斗者,狂酒者,輕露者,骨柔質(zhì)鈍者”的“五不可傳”。其后,對這方面的要求更為具體,如清末“楊氏傳鈔太極拳譜”中列有“八不傳五可授”,其中除了“不傳根底不好之人”一條外,其余無一例外都是從正反兩方面對傳人的道德要求。

習(xí)武者當(dāng)刻苦練武磨礪意志
清代乾隆年間著名拳家萇乃周曾專門訂立過一個“初學(xué)條目”,其中有這樣一條規(guī)定:“學(xué)拳宜專心致志,殫心竭力,方能日進(jìn)一日。”這是說練武者只有在持之以恒的習(xí)武過程中刻苦磨礪自己的意志品質(zhì),方能習(xí)有所成。清末郭云深的“半步崩拳打天下”,都說明了這個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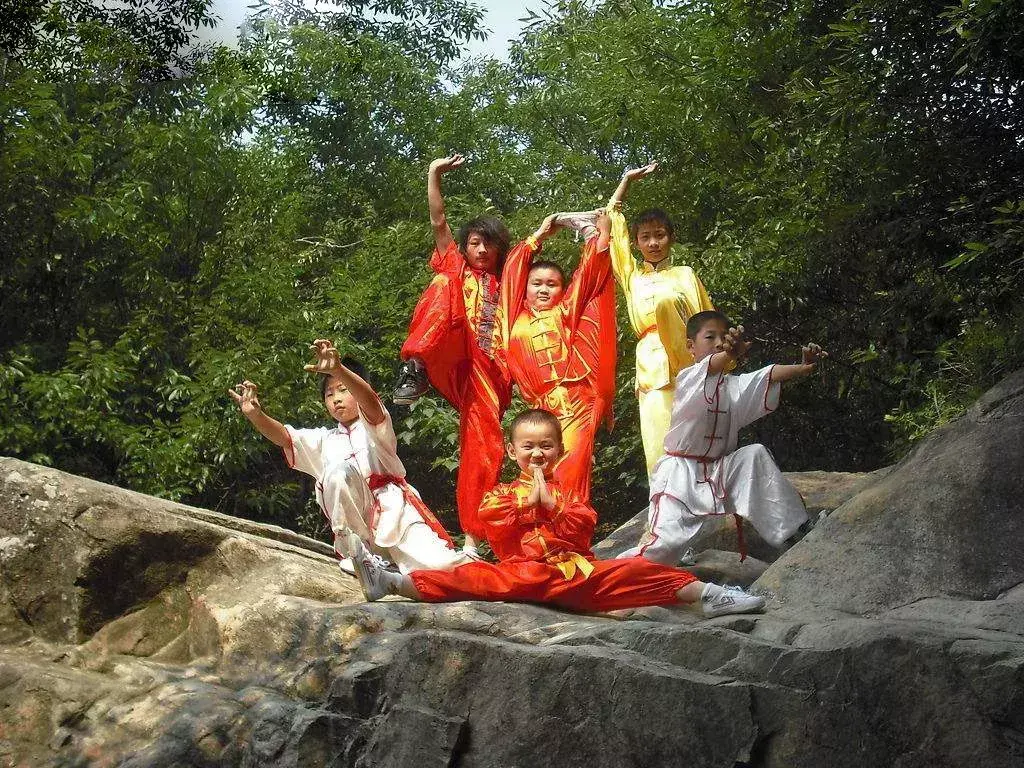
習(xí)武者當(dāng)懷仁愛之心報效國家
從明代少林武僧“保邦靖世即傳燈”,到程宗猷《耕余剩技》中強(qiáng)調(diào)的習(xí)武者應(yīng)“壯干城,靖疆圉,俾師門之指授益藉光且大”;從清代梅花拳傳人楊炳在《習(xí)武序》中說的“治四海如盤石之安,登萬民于仁壽之域”,到《少林拳術(shù)秘訣》提出的“不得恃強(qiáng)凌弱,任興妄為”和“恢復(fù)河山之志,為吾宗之第一目的,倘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等,無一不是對此內(nèi)容的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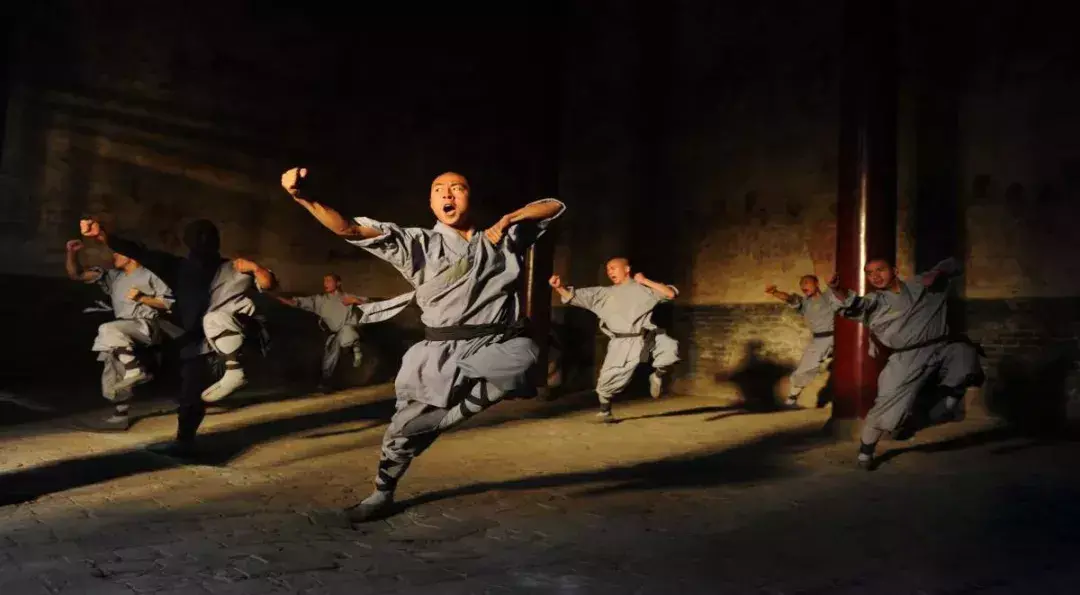
由此可見,古代武德起于先秦,中繼唐宋,終于明清,最后形成了一個內(nèi)容豐富且具有高度實(shí)踐指向的武術(shù)文化現(xiàn)象,并進(jìn)而對后世產(chǎn)生了彌久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