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導演為了突出主角的英明神武或神機妙算��,都會適時安排一位與主角能力不相上下的反派出場,上演一出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的好戲��。該劇也不例外��,當劇情發展到第十三集的時候,身居大理寺評事一職的八品小官元載粉墨登場���,成為李必、張小敬捉拿狼衛��、守護長安任務上的重要對手��。
其實���,歷史上真實的李泌�����、元載,也的確是政治上的死敵���,他們的故事遠非影視劇中上元節的十二時辰能夠展現極盡的��。
一�����、政治棋局上的旗鼓相當
歷史上,李泌和元載在仕途上達到的高度可謂旗鼓相當�����。元載因結交有從龍之功的宦官李輔國���,在唐代宗時期執掌相權���;李泌歷事三朝���,于唐德宗貞元年登臨相位��,是大唐二百八十九年歷史上數得著的名臣���?��?梢?����,兩個人當官都當到了“國務院總理”的級別,然而不同的思想境界卻注定了兩人不同的職場方向甚至不同的人生結局���。

李泌世居京兆�����,年少成名��,被譽為神童。七歲時即被唐玄宗召見。據說當時玄宗正同宰相���,也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張說觀棋。張說有心試一試李泌的才華,令其以方圓動靜作賦���。李泌問及要旨,張說隨口道:“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小李泌一聽�����,信口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一如多年后那首明志之作《長歌行》——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氣志是良圖�����。少年志氣與才情讓張說也為之嘆服。后來的開元名相張九齡亦與之結為小友。及長,上書言事���,屢屢洞中時弊。玄宗欲授官職���,固辭,乃令與太子交游���,聯為布衣交。太子常呼為先生���,不呼其名。這也是《長安》一劇中演繹的“李必是太子的人”的歷史背景���。
后來,安史之亂爆發��,李泌隱居潁陽�����。直到太子李亨靈武稱尊�����,方出山輔佐肅宗、代宗兩代帝王平息了摧殘帝國八年的叛亂,為天下蒼生亦是為了少年時的友誼。
相較李泌的忠肝義膽�����,來自鳳翔岐山的窮小子元載的上位之路充斥著圓滑世故和投機主義��。
其仕途從大理寺評事起步��,歷任東都留守司判官、大理司直等職���,還娶到了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之女為妻��,升遷之路可謂順風順水�����。再后來簡直一發不可收拾,升任度支郎中���,最后坐到了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的位子上��。其風光無限妥妥的一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勵志傳奇��。但真正翻開史書�����,這位的每一步進階之路幾乎都離不開揣摩人心的腹黑之術。
當李輔國發動政變除掉太子李豫(俶)的政敵張皇后�����,奉太子即位。元載自覺地向這位“定策功臣”靠攏���,深深取得他的信任。待這位“功臣”權焰愈張�����,唐代宗欲除之而后快時��,他又果斷地加入到這個刺殺權閹的計劃中去���。
除去李輔國,代宗準備對另一個勢傾朝野的宦官魚朝恩下手的時候��,元載再一次機敏地窺知上意��,主動替皇帝布定密謀���,翦除魚朝恩�����,至是得寵益隆,走上權力巔峰���。
這一路披荊斬棘,似乎正印證了《長安》劇中工部主事封大倫對他的評價——“我今日方才明白�����,你為何年紀輕輕便已官居八品��。你對機會的嗅覺��,實在是太敏銳了?����!?/p>
確實��,歷史上的元載也不會輕易放棄每一個上升的機會���。
二�����、不一樣的君臣之道
李泌和元載���,都具有文武才�����,而且最后都當到了宰相��,可以說是旗鼓相當。但是在對待君臣問題上,不一樣的“道”讓他們不相為謀��。
李泌崇尚道教�����,淡泊功名�����,事君常導以善,執法常引以寬。
唐肅宗即位之初���,準備授建寧王李倓為天下兵馬元帥,討伐叛軍。李泌以太宗李世民的例子勸諫肅宗應將兵權委任皇長子廣平王李俶,消弭了一場潛在的“玄武門喋血2”的隱患。后來唐肅宗誤信張良娣���、李輔國讒言,賜死建寧王���,廣平王李俶懷著兔死狐悲的觀念���,欲除去輔國�����、良娣��,李泌及時勸阻��,“能盡孝道,自足致福�����。良娣婦人��,不足深慮��,但教委屈承順,包管前途無礙?�!睆V平王恍然大悟���,遂忍辱負重���,韜光養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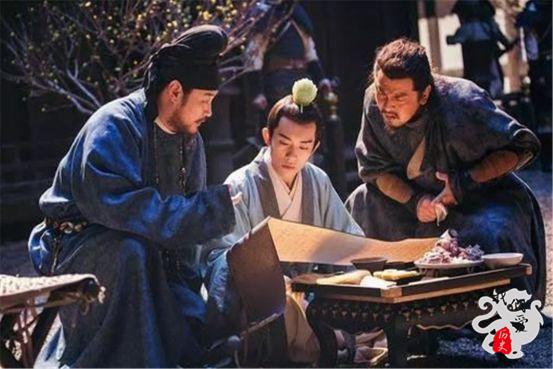
唐德宗時�����,同平章事張延賞企圖利用太子妃生母郜國長公主私通禁衛將軍李昇的事件搖動東宮。關鍵時刻��,又是李泌出手��,直言規諫���,“愿陛下勿信讒言��!即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尚當辯明真偽,難道妻母不法�����,女夫也宜坐罪么��?臣敢以百口保太子�����。……”一場易儲風波有驚無險�����!
此外還有一件妖僧作亂的公案���。時有妖僧李軟奴勾結殿前射生韓欽緒等�����,潛謀作亂�����,事發被捕�����,德宗命內侍省鞫治��,李泌密上一疏���,略言:“大獄一興�����,牽引必多,國家甫值承平�����,不應輾轉扳引��,致失人情�����,請將李軟奴一案出付臺官鞫治。”德宗俯允�����,即命把全案移交臺省��,至審訊結果��,罪止李軟奴、韓欽緒兩人�����,朝臣無一牽連���。這都是李泌李鄴侯暗中挽回��,了結一場巨案。清原正本,無愧社稷之臣���。
反觀元載,政治生涯的高光時刻莫過于以宰相之尊,幫助唐代宗鏟除以魚朝恩為首的閹黨��。若只看結果��,確是大快人心的好事�����,然究其心跡,無非選擇性站隊�����,為獲取政治資源不擇手段���,至于需要清掃的對象是忠君賢臣還是奸佞小人���,則不在他的考慮范疇之內���。所以�����,所謂的翦除閹黨�����,不過是大唐官場的一幕“黑吃黑”鬧劇��。后人對于其人品的憎惡自然多于對其“功績”的認可���。
三�����、迥異的人生結局
由于善于鉆營�����,加之對政治風向的精準辨別能力。元載的仕途似乎比李泌順遂的多��,在肅宗與代宗權力更迭的時候便已經穩居相位���。
權力的魔力逐漸讓他迷失了自我��,或者說是原形畢露���。他似乎忘記了那些被他踩在腳下的政敵��,也曾是這個帝國的狠角色,也曾像他今天這樣站在權力的頂峰,睥睨一切���。
“我站在臺上,卻毫不心慌……”此時此刻元載只想高歌一曲�����,一抒壯志��。春風得意的元載終于按耐不住心底的欲望,恃寵生驕���,開始排除異己、結黨營私��、中飽私囊�����,朝臣中敢于反對他的人���,輕則貶官外放�����,重則嚴刑致死,狐貍尾巴終究是藏不住了�����。
在一長串的打擊異己的名錄里���,李泌赫然在列���。因為元載心里明白�����,雖然自己身居高位���,但無論是才學還是影響力都遠不及李泌�����,嫉妒永遠是伴隨著野心家一起成長的罪惡因子���。

在元載的排擠下�����,李泌去江西做了個判官�����。值得一提的是���,當年任刑部尚書的顏真卿也是因為得罪了元宰相��,被貶到陜州做了個別駕。
正當元載在為自己的“功業”自鳴得意的時候���,孰不知自己的喪鐘也快要敲響。唐代宗很早便發現了元載的野心��,將顏真卿���、李泌相繼外調��,與其說是貶官不如說是對功臣的保全�����。至于元載,皇帝不過是在等一個機會���。
大歷十二年三月��,有人密告元載與另一個宰相王縉密謀不軌���,由代宗親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率禁軍收捕���,囚系政事堂���。令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聽�����、禮部侍郎常袞等公同訊鞫��,最終當然坐實罪證���,元載按律賜死�����。
權力的夢醒了,生命也即將走到盡頭��,想必此時元載方才明白��,他和李輔國���、魚朝恩們沒什么不同�����,只是暫時寄居于高位而已��,一旦跌落�����,粉身碎骨。
據說元載受刑時曾求速死���,刑官冷笑著說:“相公入秉國鈞,差不多二十年���,威福也算行盡了,今日天網恢恢��,親受報應,若少許受些污辱��,亦屬何妨��?��!?strong>說完竟用襪子塞入元載口中�����,慢慢縊死,死狀極慘��。
元載死后�����,他的妻兒子女一并正法��,家產籍沒���,財帛萬計��。即如胡椒一物��,且多至八百石��,俱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各官。

不久代宗駕崩��,唐德宗即位�����,朱泚���、朱滔��、李懷光�����、李希烈等藩鎮節度使相繼叛亂,這時形同大唐柱國的郭子儀已經去世�����,李泌再次奉召出山���,在六十歲上下的年紀等來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三春��,懷著對家國天下的執念,幫助德宗逐一平息叛亂�����。唐德宗望著眼前這位自己爺爺少年時代的摯友感慨萬千�����,將帝國宰相的權杖遞到他手中��。李泌也不負眾望,或者說他從來都沒讓大唐失望過。
在宰相的位子上,他依舊謙虛謹慎���,為君盡職盡忠,為民殫精竭慮,救荒濟乏,挽救時弊���,直到六十八歲,駕鶴西歸,留下神仙宰相的美名���。
四、“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道理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老子《道德經》里的經典語錄。一生信奉道家思想的李泌顯然比元載更懂得這句話的含義��。
元載一生鉆營,卻始終沒能參透“不爭”的玄機。這是兩位大唐相爺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注定他們一生造化的命門所在���。
因為精于算計,元載贏在了起點;因為夫唯不爭���,李泌贏在終點。
現代職場中,元載一樣的人很多,李泌一樣的人卻不多。元載這樣的人,聰明�����、世故��,有理想,有目標���,能夠準確揣度領導的心思,自認為一切盡在掌握。其實你把領導當傻子的同時領導亦把你當棋子而已。
李泌這樣的人��,當真看破紅塵��,淡泊名利嗎��?也未必,若真如此,當年被元載排擠去江西的時候就該退隱衡山�����。斯人心中���,自有一番抱負�����。只不過李泌的聰明之處��,就在于“不爭”。

肅宗靈武登基時�����,欲任為右相���,李泌固辭�����,“陛下屈尊待臣���,視如賓友,比宰相顯貴得多了���,臣有所知,無不上達��,何必定要受職��!”此時的不爭是因為寸功未立��,驟居高位,情難服眾�����。
元載得志時��,嫉賢妒能��,李泌遭排擠外調,亦能欣然受命�����。此時的不爭是為敵強我弱��,暫避鋒芒��。
受職同平章事時,德宗面諭��,“朕今與卿約���,卿慎勿報仇。如他人有德及卿���,朕當為卿代報?�!崩蠲趶娜菪Υ穑骸俺妓胤畹澜?����,不愿與人為仇,從前李輔國�����、元載均欲害臣�����,今皆死去了���。就是臣的故友���,或早已顯達���,或已淪亡��,臣亦無德可報,臣今日愿與陛下立約,唯愿陛下勿害功臣���!”即便位極人臣,仍言不及私怨、私恩�����,可謂通透至極���。
人在江湖��,職場亦或官場���,機巧圓滑、八面玲瓏者大有人在,然而真正能夠悟透“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恐怕真的沒有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