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3期選載葉淺韻《生生之門》“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之際,本刊“非虛構”欄目推出“女性書寫小輯”,以四篇風格、取材截然不同的作品,呈現女性書寫的不同面向:身體與靈魂、生育與勞作、成長與衰老、情感與思辨……今日推薦的是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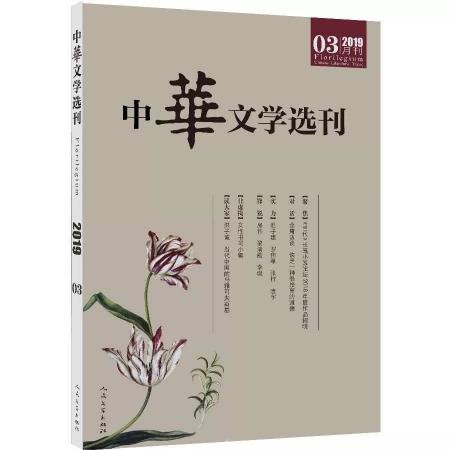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3期選載葉淺韻 《生生之門》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之際,本刊“非虛構”欄目推出“女性書寫小輯”,以四篇風格、取材截然不同的作品,呈現女性書寫的不同面向:身體與靈魂、生育與勞作、成長與衰老、情感與思辨……今日推薦的是葉淺韻《生生之門》。
葉淺韻|女性書寫小輯
葉淺韻,曾用筆名“大彩”,1976年生,云南宣威人。著有《陌上花開時》《必須有那樣一個人存在》等。
1
懸在針尖上的命
——《生生之門》創作談
晨早起,見青霜和冷月在天地之間遙望,寒意頓襲。窗外的鳥兒,已經叫醒一片林子。生存的秩序,在萬物之間打開了新的一天。二胎政策的話題漸漸冷卻,就像吹過一陣猛烈的風,帶來歡喜和哀愁。一些人圓了,另一些人缺了。
有幾個腆著大肚子的中年女人路過,她們的臉上除了妊娠斑,更有一種迎接新生命的歡喜。孕育生命是一個神奇的過程,一粒小小的種子,一天天,一點點長大,成為嬰兒,成為人類的希望。而一些冰冷的器械,它們進入過女人的身體。血淚、疼痛和死亡像新生的影子,隨行一生。自造物主把孕育生命這個神圣而偉大的任務降臨女人身上時,一個個永不停歇的生死場,在一代又一代女人身上鋪開。
從一結婚肚子就沒閑著的祖母輩,到計生政策開始做了結扎的母親輩,到我們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的別無選擇,再到這一陣風吹來。女人的命就像被懸在一枚枚細細的針尖上。生而為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尋自己心中的圓滿。女人們更是有一種拼了命的悲壯。有了女兒的,特別想要一個兒子。有了兒子的人家,也特別想要一個女兒。但如果能再有一個兒子,對于父系會更有喜感。他們容易扯到家族的勢力和榮譽之上,像是一個兒子就能成就一個村子,一個兒子就是一支隊伍一樣。
一項政策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在離土地最近的地方,熱鬧非凡。女人的身體也是土地,人類在土地上繁衍生息,并盡力想從土地上獲取最大的收益。一些高齡產婦冒著生命危險,為了圓恰自己和家庭的美夢,堅定地走在生產二胎的路上。在未成為悲劇之前,人們通常以喜劇來謝幕。仿佛只要有生的歡欣,死的恐懼就變得微不足道。
那些年,村子里的女人因為難產而死去的,屢見不鮮。就是到了現在,醫學的手段先進了,也依然在所難免。然而,這個社會對待女性的態度不容樂觀,許多人總是在土地上獲取收益之后,就忘記了土地的種種好處。遠遠不可能會是歌德所寫“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上升”。我們習慣了在男權社會里用逆來順受來消滅一切不幸,甚至成為他們的同謀者。而悲劇的誕生,永遠少不了幫兇的角色。從村子里婆婆對生不出兒子的媳婦惡言相向,到城市里女性之間為博取上位毫不手軟的狗血劇情。那些帶著女字旁出生的漢字:嫌、嫉、妒、奴、奸,無一不昭示著萬惡的源頭。
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傳統和封建構筑的堡壘下,我的聲音也會是微弱的。在死亡面前,我們面對生,是顯得潦草的。我們對于生命的思索也是有限的、無奈的、無知的。
但身為一個女性寫作者,我無法忽視同類的生存狀態。許多見聞和經歷壓在胸中,堆積成塊壘。夜深無眠時,那些長滿蒼綠的痛覺從骨縫里爬出來,被隱性的細節打開、合上,像一股混濁的暗流,等待時間的清洗。之前我曾寫過一個中篇小說,題材亦是女性的生育,在作了很多鋪設之后,卻觸摸不到我想要的那一個點。那篇小說也發表了,但它就像一個半成品,顯得粗糙和黯淡。
我困惑于找不到恰當的方式來呈現幾代女性生育的史詩悲歌,在不斷的思考中,我想要抵達的地方漸漸變得清晰起來。對于女性,那一道門,過去了是生,過不去就是死。可我們沒得選擇,就像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性別一樣。我決定用坦誠的敘述方式,撕開自己的內心,剝離出女人面對生育的勇敢、無助、痛苦、喜悅、哀愁。
寫這篇文字的過程,對于我來說是疼痛的。有些像一個不懂世故的野丫頭,非要扒開衣裳讓別人看自己的隱私,向人毫無心機地訴說它們曾經受過的傷害。在未生育之前,我所看到的文字對于生育的描述顯得過于隱蔽和輕微,就像山上吹來的一陣風輕輕搖動了樹梢。以至男人們要用擠蠶豆米來形容,一陣笑聲過后的凄楚,唯有經過生產的女人才能感知。當我面對生育的時候,它給我的身體帶來疼痛和傷害卻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它是直白的、洶涌的、毫不留情的。我以為我會死掉。
女人在生產之后,像是所有的羞恥和尊嚴都被降低了規格。再苦再難的生活,就有了最大限度的韌性。被拓寬了的生存際涯,讓女人能匍匐軀體,抵抗庸碌,也創造奇跡。她們就像大地一樣,可以生長萬物。母在,家在,安在。當我的孩子對我說,世界上最貴的房子是媽媽的子宮時,我頓時被一圣潔的光輝所籠罩,覺得一切苦難都是值得的,它讓我的生命在另一個生命身上延續得這般美好。
如果不是新出臺的這項政策,人們已經習慣了固有的思維,一個孩子沒有什么不好。就像當年沒有計生政策的時候,覺得要多子多福才好。傳統和風俗造就的生活方式,被一代代人恪守和打破。當一種生活的秩序被打亂之后,人們需要很長時間來辨識和適應。而這個過程中出現的生生死死,離離合合,總是帶著時代鮮明的烙印。作為一個在場的寫作者,我應該把我所看見或是經歷的這些忠實地記錄下來。它只是我的一管之見,也許還帶著自我出身的偏狹、局促和無知。但請慧眼之人明辨和思諒。
這篇長散文的初稿寫了四萬多字,從一條浩浩湯湯的大河寫進了小溪水的狹窄里,后半部分幾易其稿,終不能算是最滿意的。定稿為二萬五千字,二萬五千字的長散文,于我而言就像走了一回二萬五千里的長征。而女性生育的長征,是永遠只有新開始的長征。它被一個又一個女人,用身體一一丈量。不管這篇文字能成為什么,這也是我自己生產的一個孩子。我衰老的子宮已經不能承擔一個新生命的降臨了,我就把它當作我的孩子吧。寫完這篇文字的時間是2018年5月29日。如果我腹中的胎兒安然,正是她降臨人間的預產期。合上文字,我的眼淚和心一齊碎在地上。
——轉自十月雜志微信
2
生生之門(節選)
夢里有殺戮和偈語,砒霜和蜜糖,都在神的手上。生與不生,都是命。
——題記
1
一道門,隔著簾子。無風的盛夏,簾子嘩啦過來,嘩啦過去,人進一趟,出一趟。呻吟,痛苦的呻吟,從昨天下午太陽落山時開始,就一直沒有停過。家里的氣氛變得有些奇怪,說是二伯母要生產了,但我感覺不像在迎接一個新生兒,倒更像在恭候一個敵人。我爺爺已經把大門的門檻撬了,他說,要向什么神仙投降,以表誠心。
我父親和母親一大早就去后面山上種苦蕎了,說要趁著剛刨完洋芋,地軟,有余肥,把苦蕎撒下去,那幾塊地夠他們忙活一整天。出門前我奶奶在鐵鍋里烙了幾個苦蕎粑粑給他們帶著當午飯,剩下的一些放在簸箕里晾著。我最不愛吃那個鬼東西,又苦又硬,偶爾家里會得一點點蜂蜜,苦蕎粑粑蘸著蜂蜜倒是會有一些滋味。我知道說餓了,奶奶會讓我啃一個苦蕎粑粑。我才吃了一口,苦涼的味道就從舌尖爬上了眉頭。這時候,我奶奶愛說那一句老掉牙的話:苦蕎粑粑才動邊!村子里的人都會這么說。她們用這句話來比喻自己不喜歡的生活才剛剛開始,一口下去,才動了個邊邊角角,辛苦的日子還早著呢。天然的宿命,是村子里的人不可抗拒的選擇。苦蕎不好吃,但必須要吃,能有苦蕎接個口讓家里人不餓肚子,這已是神的恩賜。我奶奶總愛講起她們那個年代吃樹葉吃草根的故事,好像能吃飽肚子已然是一種應該知足的生活。
屋里,二伯母還在呻吟。那聲音讓我想起去年臘月里的事,那頭黃毛豬被幾個人用繩子縛綁起來抬上案板,它無力的反抗和哼叫,帶著絕望和無助。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時,它叫喊的聲音漸漸弱下來,四只腳機械地滑動了好幾下,然后,它就死了。我手上的苦蕎粑粑被我啃了半邊后,就放在手里玩弄著,我奶奶沒好氣地說,你這姑娘,肚子里有點數了,就要開始糟蹋糧食,吃不完就放回去,給你爹晚上回來吃。
我奶奶派我二伯去三十多里開外的地方,請了個接生婆回來。說是接生婆,卻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我奶奶的火“噌”一下就到了腦門心,她尖著小腳怒氣沖天地站在她的二兒子面前,說,命,人命,都快要活不得了。你說哪回讓你出去做的事情,你是給老娘辦圓恰了的。我二伯有些口吃。他說,去,去,去大村子請了王婆婆,她,她,她家,她家,她家里人說,她,她,她,她……“她”了半天還沒“她”出后面來,我奶奶說,她該是著老鷹叼克掉了。我二伯頭上的青筋冒出老高,總算把他要表達的意思說完整了。原來,王婆婆騎著她的小白馬去了四十多里路上的大山深處幫人接生去了,是昨天半夜里走的。王婆婆的鄰居是好心人,她說,救命要緊,快去對面那山上請了繆仙家去,神藥兩解也可保個萬無一失。我二伯腳下生風就去請了繆仙家。
屋子里傳來我二伯母虛弱沙啞的聲音,她像是用盡所有的力氣在喊叫,媽,媽,快拿牽豬刀來。我奶奶說,我的兒呀,繆仙家來了,你忍著,忍著哈,他會有辦法的。牽豬刀,事實上是叫殺豬刀。但在這個家里,篤信菩薩的奶奶見不得“殺”字,她說殺生是一種罪孽,該回避的要回避一下,省得沾染了邪惡。一個“牽”字,是死的另一種生,是豬的一種命運。豬的生死都掌握在人手里,而人的生死,也許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在繆仙家神神叨叨的咒語里,仿佛我眼前的這個世界都被一種無形的東西主宰了。他敬完各路鬼神,轉身從他洗得發白的帆布包里掏出舊紗布、剪刀、鉗子等。奶奶端來一盆熱水,他的一雙手在水里來回地搓洗,我奶奶說,仙家,沒什么洗的,就有點鳳尾稈子燒成的堿灰水,你將就著洗下吧。家里的洗滌用品都是純天然的,除了堿灰水,還有白泥沙和皂角樹上結的皂角。繆仙家用手抄了兩把堿灰水,又用清水沖洗了好幾道。屋子里又傳來我二伯母的聲音,她說,我要死了,快讓我死了吧。
簾子一動,我奶奶和繆仙家都進去了。我曾悄悄地掀開過簾子,偷看二伯母,她睡在光光的板床上,下身赤裸,肚子像一只巨大的南瓜,圓滾滾地側在一邊,身子下邊淌了一大攤水漬,頭發被汗水浸濕了,嘴唇青紫,面容扭曲。我輕輕地喊了她一聲,她沒理會我。我趕緊就出來了。
這村子的周圍都種滿了竹子,毛竹、金竹、紫竹什么的,到了夏天的樹蔭下,三五成群閑來沒事的姑娘媳婦們,不是在使針線,就是在編竹簾子。每一道門上的簾子,就成了一種廉價物美的裝飾,算是給貧窮的屋子添了點小風情。哦,對了,風情這種詞匯在村子里是沒有人知道的。只有在如今的回憶里,那些苦難貧窮中不一樣的響聲才會多出幾分韻致。
除了簾子,我還對木門和窗子保留著一些特殊的記憶。盡管后來在一場大火中,村子里一家挨著一戶,一戶連著一家的房子都燒毀了。那些鏤空雕花的窗子、木門,以及透著神秘氣息的百年供桌,一切都散發著古老陳舊的味道。夏日的早晨,一個一個小腦袋從樓上的窗子里伸出來,咯咯咯地笑著,瓦檐下的紅辣椒和大黑貓就醒了。我們風一樣地穿過田野,去捉蟲子,去找豬菜。遇見蛇,遇見蝴蝶。被蜂叮過,被狗咬過。
一村子的調皮娃娃,哭聲,喊聲,笑聲,吵鬧聲,日子就像夏天的日頭一樣火熱。每一個孩子都吃過父母的棍棒,村子里的人說這叫“吃跳腳米線”,那些從山上弄來的細條子,一打一條白痕,痛得直跳起腳來。我奶奶總愛護著我,她說,只要不憨不包的娃娃,哪一個又是依你大人打整來著,你叫他往東他就往東,叫他往西他就往西的時候,怕也是急死幾代人的憨貨。我母親就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丟下棍子匆匆去了地里。有時我摔了一跤,腦門都出血了,我奶奶也一邊哄我一邊說,摔哈打哈就肯長了。就算是有一次偷了鄰家的瓜果被人咒罵,我奶奶也說,咒哈就咒哈了,咒哈肯長。肯長和長大,在村子里是一種希望,就像每一個家庭里養著的小豬兒,主婦們盼望著它們肯吃肯長一樣。
二伯母又叫喊了起來。我爺爺手上的長煙袋一直在冒著細煙,他吧嗒吧嗒地咂著一鍋又一鍋的旱煙,已經去樓上的“天地君親師位”之前的香爐里點了幾回香了。繆仙家叫“使力”“使力”……二伯母的聲音越來越虛弱,我奶奶一盆一盆端出來的水都是紅色的。看著那些紅色,我想起了前些天我從樹上摔下來,腦門上的血順著臉頰淌下來,我奶奶幫我包完傷口后,洗臉洗手的水全都是紅的,我一直止不住哭聲,以為我會死掉。我鉆進爺爺的長衫里,聞著他身上又臭又有隱約香味的特殊氣息,心里一陣又一陣害怕。若是往常,我爺爺是要撓我的胳肢窩里的癢癢的,我也要摸他下巴上的長胡子玩的。
繆仙家的聲音:“使力,快使力,看得見頭了……”“谷哪,谷哪……餓了,餓了……”洪亮的嬰兒啼哭聲音傳來的時候,我爺爺丟開嘴里的煙袋,使勁地拍了一下他的大腿說:“菩薩保佑,肯定是個帶把的,聲音這么大。”他說完隨手捏了捏我的臉蛋,眼睛里滿滿的歡喜像是要溢到我身上。我奶奶說,孫子,孫子,我的孫子。全家人一下沉浸到添了男丁的喜悅里,二伯母剛從鬼門關上打了一個轉兒的事,倒是被大家給冷落了。仿佛有了生的降臨,死就顯得那么微不足道了。
繆仙家的臉上掛著汗珠子,像我父親從后山上背了重活路回來,一口氣歇在石坎上,額頭上的大汗像不停息的小溪流一樣,直到他抽完一根草煙。繆仙家清洗著那幾塊紗布,一盆又一盆浸著二伯母鮮血的水,潑出去,又潑出去,重復了不知多少遍以后,那幾塊紗布終于見到點白色的痕跡了。繆仙家把它們放在水里煮沸了,才晾曬在外面的柴堆上去。
第二天早晨,二伯抱著一只紅公雞給丈母娘家報喜去了。我的眼前又出現繆仙家一盆一盆潑出去的血水,想起這村子里的人愛說的一句話,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潑出去的水都浸到了土地里,轉眼兒就不見了影蹤。那它們都去哪兒了呢?南山嫁了一個姑姑,北山又嫁了另一姑姑,她們都是村子里的客人,只在一些特別的日子里,回來看看,又馬不停蹄地回去了。這方圓團轉村子里的人說誰家嫁女兒這事兒,還有另一種說法,叫打發姑娘。誰家定了嫁女兒的日子,就會說,某某人家哪天打發姑娘,要吃個酒去。
有了孫子的爺爺,像是在他的血脈里注入了興奮劑。那個晚上,他在夢里唱起了情歌,“啊,隔河的哥哥望見妹爬坡,頭發辮子往后拖,我的小情妹……”大概是他想起了他年輕趕馬時的那一樁往事,為了糧食,他用馬馱著村子里的鄉親們用竹子編制的籮筐、背篼、簸箕等,翻山越嶺去貴州換糧食。曾經有一年遇上災荒,生意難做,一路雨淋日曬,回到家糧食全都出芽了。爺爺講的故事里曾有一個頭上戴著大飾品的新婚娘子,那飾品足足有簸箕那么大。在我們村子里這樣裝扮的一定是七老八十的女老人了。爺爺一開口就叫人“大媽”,待回過頭來,才知是個俊俏的小妹。
生了兒子,二伯母在這個家的地位明顯高出了一篾片,對,一篾片,這是我母親在挑水歇氣的時候跟人說的。村子里的竹子常常成為她們比喻什么東西時候的參照物,比如說,太陽升起一竹竿了,打核桃就打了幾竹竿,小菜出了篾片高了什么的。竹子已成為一種言語上的秩序,就連對生育稠密的女人們,她們也會說,就像春天出筍,一個趕著一個。那時,我不知道生男生女的概念意味著什么,但對于連接生了三個女兒的母親,這聽上去氣不順的話語,得到了與她同樣境況的幾個嬸娘們的響應。她們的語氣里都有一種生不著兒子不罷休的堅定。
村子里有一戶人家已經連生了八個女兒了,那個我要叫五伯母的女人佝僂著腰挑水的時候,我又看見她鼓起的肚皮。……
全文見《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第3期
選自《十月》2018年第5期
新刊目錄
聚焦│Focus
《當代》長篇小說論壇2018年度作品揭曉
閻晶明 現實主義與現代性的融合
實力│Main Current
遲子建燉馬靴(短篇小說)
選自《鐘山》2019年第1期
羅偉章寂靜史(中篇小說)
選自《鐘山》2018年第6期
張 檸劉玉珍,叫你那位羅長生來一趟(短篇小說)
選自《人民文學》2019年第1期
薛 舒成人記(中篇小說)
選自《長江文藝》2019年第1期
班 宇猛禽(短篇小說)
選自《上海文學》2019年第1期
郭 爽拱豬(中篇小說)
選自《正午時踏進光焰》
鋒銳│New Wave
房 偉 陽明山(短篇小說)
選自《紅豆》2019年第2期
梁清散 濟南的風箏(短篇小說)
選自《銀河邊緣 · 奇境》
李 誕在雪地猶豫(短篇小說)
選自《冷場》
非虛構│Non-fiction
女性書寫小輯
葉淺韻生生之門
選自《十月》2018年第5期
魚 禾寄居之所
選自《天涯》2018年第6期
草 白臨淵記三題
選自《野草》2018年第2、3、6期
呂 途女工傳記四則
選自《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
讀大家│Reading Classics
洪子誠死亡與重生?——當代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
選自《文藝研究》2019年第1期
對話│Dialogue
金 庸張 英俠是一種很崇高的道德(訪談)
選自《青年作家》2019年第2期
書架│Book Shelf
潘向黎 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外三篇)
選自《梅邊消息:潘向黎讀古詩》
肖像│Portraits
王祥夫寬堂先生
選自《滇池》2019年第1期
藝見│On Arts
朱以撒書意六譚
選自《書意百譚》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改版擴容
以更豐富的內容服務讀者
每月1日出版,定價20元
郵發代號82-497
全國郵局均可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