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雨前產經觀察:羅提邱娟虎嗅:雨林下編者按雨前產經觀察&虎嗅聯合出品雨前產經觀察與虎嗅共同策劃「中西部城市觀察」系列報道,從區域發展視角進行深度調研,為地方產業升級和空間有機更新提供參考。此為系列第一篇,我們聚焦「中西部城市承接產業梯度轉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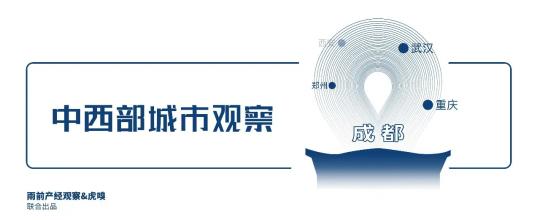
雨前產經觀察:羅提 邱娟
虎嗅:雨林下
編者按
雨前產經觀察&虎嗅
聯合出品
雨前產經觀察與虎嗅共同策劃「中西部城市觀察」系列報道,從區域發展視角進行深度調研,為地方產業升級和空間有機更新提供參考。
此為系列第一篇,我們聚焦「中西部城市承接產業梯度轉移之后」的諸多問題進行探討。
身處中西部的城市,如何才能長出萬億級龍頭企業?
這令很多地方政府輾轉反側,求而不得。
然而,一座“老、少、邊、島、貧”的三線城市做到了。2007年,這座當時連火車都沒通的三線城市,與一家中小企業簽訂了投資建廠協議。
誰料,這家不起眼的企業后來竟生長出一個行業巨頭,市值甚至一度超過中石油。
這座三線城市叫寧德,中小企業叫ATL,長出的龍頭叫CATL——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的崛起在于掌握了新能源汽車的電池核心技術,而動力電池在大規模商用化后,制造產能也開始向中西部擴張,其中四川省就承接了多個項目。
2019年至今,寧德時代與宜賓陸續簽訂了六期項目,總投資超300億。今年起,蜂巢能源投資71億先在遂寧生產鋰離子動力電池的電芯模組和電池包,又在成都東部新區簡州新城投資220億建動力電池制造和研發基地;璞泰來投資140億在成都邛崍建設新能源電池材料全產業鏈項目;中航鋰電也投資280億在成都龍泉驛區建動力電池及儲能電池成都基地。
這些項目誠然為四川就業、GDP與產業鏈集聚帶來了好處,但在“尾雁緊隨頭雁”的雁行發展模式中,地方扮演的仍是尾雁追隨角色,顯然無法與寧德案例相比。
實際上,十幾年前四川就承接過一波電子信息與汽車制造業的梯度轉移,富士康工廠從沿海轉到成都、重慶、鄭州多個中西部城市,成千上萬的廠妹夜以繼日在流水線上勞作。
流水線上女工在忙碌作業 | 圖源:視覺中國
歷史似乎又在重演?
并不。這次不光有成熟產業的梯度轉移,還有產業變革的新老交替。新興產業的爆發正在為中西部城市孵化龍頭企業留出機會。
瞄準種子,提前鎖定企業
早期寧德引進ATL依然是梯度轉移。
一開始公司創始人曾毓群只選擇了在寧德建幾個廠房,總部和主體仍留在東莞。后來寧德能反客為主,既得益于曾毓群的鄉土情結,也與新能源的產業特點有關。
以往化石能源時代,能源具有強資源品屬性。中東遍地是石油,山西產煤全靠開采,企業必須就近作業,不可能直接搬遷工廠。
而新能源的制造業屬性遠大于資源品屬性,曾毓群建廠不用考慮當地是否有鋰礦。且鋰電池屬于新興產業,對區域、周邊產業結構要求不高。
既然到哪建廠都差不多,何不回家鄉?
ATL在寧德建廠后,管理和研發也陸續跟過來,一方面在于曾毓群的號召力和高薪吸引(寧德工資比東莞高30%),一方面在于鋰電池的制造業特性。
鋰電池的基礎研發屬于材料學,依賴實驗對化學元素的不斷組合試錯,很難一夜突破,因此創新周期非常漫長。索尼1990年就發明了鋰電池,直到前不久寧德時代才宣布在鈉離子電池上重大突破,一晃三十多年。
在材料體系創新的大周期內,鋰電池品質與能量密度的提升有賴工藝及經驗改進。在寧德時代,工藝崗是要下產線的,工藝發生任何細微變化都會不可預測地改變產品特性,研發與制造的緊密程度越高,越有望實現創新突破。
當然,這只是初始工廠制造與研發高度結合。
當一項工藝成熟大規模商業化之后,寧德時代在其他地方擴建的工廠就是標準化生產了。
類似計算機、電子產品,行業工藝成熟度高,模塊化生產程度高,制造與研發的分離度就高,聯動關系就弱。
此外,寧德政府在人才引進上下了大力氣,實行高級人才個人所得稅減免、一些專家甚至可以在當地享受到廳處級干部的醫療待遇,寧德時代員工的工資里面還有專門的政府補貼。
新興產業的高端制造業屬性,創始人的鄉土情結,政府的人才引進政策,決定了寧德招來第一個工廠后的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實現了梯度轉移的逆襲。
這給人啟示,地方政府要突破產業鏈招商的思維限制,深入研判新興產業,瞄準種子企業,搶在其將擴大產能之際積極引進。
企業擴大產能說明市場需求向好,是實力與產業有前景的證明,但如果沒有政府前期的慧眼識珠,一切也無從談起。
毫無疑問,幾乎所有中西部城市都想復制寧德案例。那么,面對新興產業如何提前研究并鎖定種子,是當前政府招商引資最應聚焦的。
招大引強,成長性與忠誠度不高
只要抓住一個產業變遷窗口,城市就能快速實現能級跨越。
20年前,成都、重慶、鄭州這些中西部城市正是抓住了電子信息制造業的梯度轉移機遇,將英特爾、富士康、惠普、戴爾、聯想等巨頭的產線瓜分殆盡,GDP排名迅速上升。
于是招大引強成為這些年政府招商引資的信仰,各領域的500強名單幾乎人手一冊,為同一家公司爭得頭破血流。
但繼續延續這種產業招引邏輯存在一些潛在問題。
其一,名花有主。上一輪產業遷移已告結束,電子信息、汽車制造幾個大產業的城市歸屬基本上塵埃落定。
其二,僧多粥少。大項目數量少容易引發惡性競爭,即便花費巨大成本成功引進,最后算總賬或得不償失。
其三,鳳尾長不出鳳頭。中西部城市引進的大項目,大多是梯度轉移的末端環節,橫向變粗易,縱向長高難。
總體而言,過去中西部城市承接東南沿海的產業梯度轉移,實際上是沿海地區承接美日韓產業梯度轉移的延伸,如深圳富士康、上海英特爾搬遷。
成都富士康總部 | 圖源:東方IC
對比沿海,中西部城市存在人才吸引力不足和地理位置偏遠難以融入國際分工等天然弱點。
很多中西部城市都存在一種現象:本土公司很難做大,但本土能人走出去,反而把公司做大了。
而且,中西部城市承接梯度轉移的多是企業生產部門、代工廠等分支,引進的人才是職業經理人而非創業者,這些項目重度依賴總部規劃,缺乏自我生長機制,一旦上面調整,說裁撤就裁撤。
這意味著,無論是內部能人支撐,還是外部環境刺激,都不足以令中西部城市在短期內從產業鏈底端爬升出國際一流公司。
即便是先進的東南地區亦如此。2010年富士康大舉內遷,高峰期有40萬人的深圳龍華富士康一時人心惶惶,配套企業蠢蠢欲動,南方都市報甚至發出了《富士康搬遷致產業鏈斷裂 龍華科技城或將擱置》的報道,雖然后來龍華富士康并未如傳言搬走,但著實給深圳敲了一記警鐘。
今年3月,富士康宣布擬定增45億人民幣在越南建設工廠。目前,富士康估計已經約有30%-40%的產品線在中國以外的地方,而且這一比例可能還會上升,逐漸搬出中國預判只是時間問題。
另一廂,員工最多時高達18萬人的三星中國是實打實撤離了。2018年開始三星就相繼關閉天津、惠州的手機工廠,2020年又關閉了位于蘇州的筆記本電腦生產線。
擁有強大供應鏈、交通信息網與高效政府服務的東南城市尚如此,中西部城市更要考慮梯度轉移來的工廠流動風險。
相比而言,東南城市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做大了本土企業,實現了產業鏈升級,不懼工廠搬遷帶來的空心化。但中西部城市的產業結構更為脆弱,一有風吹草動,很容易打回原形。
內生企業做大尚需時日,梯度轉移企業的成長性與忠誠度又不高,那么,中西部城市如何基于本地特點掌握發展主動權實現產業升級?
資源+科技,偏遠新疆逆天改命
如果說寧德主要是占了天時地利的運氣,那么新疆光伏的崛起則更多體現了人為布局的前瞻。
目前,新疆形成了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石河子和奎屯、阿拉爾為兩翼的硅材料、太陽能電池/組件封裝、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集成制造業基地。
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硅業分會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我國多晶硅產能為49.5萬噸/年,預計到2021年底,產能將達到54.4萬噸/年,產能全球占比接近80%。其中,新疆約占全國產能57%,占據光伏上游的絕對領先地位。
科創板市值1300多億,僅次于中芯國際排名第二的大全能源就是一家新疆公司,來自2011年招引的江蘇項目,如今研發與制造都在新疆。
有意思的是,大全能源創始人徐廣福與無錫尚德創始人施正榮都是江蘇揚中人,無錫尚德破產,除了歐美雙反市場需求萎縮,還在于硅料成本居高不下,徐廣福在同鄉跌倒的地方站了起來。
太陽能光伏硅料的純度,要達到99.9999%以上;電子級硅料純度,要達到99.9999999%以上。可見硅料生產,都是極致精細化的提純過程。
這個環節具有一定的技術壁壘和壟斷性。在光伏硅料的基礎上,大全能源打算進一步提純進軍電子級硅料,這是個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前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恩哥1997年提出來做第三代半導體碳化硅(SiC)單晶,最早投資支持他的就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后來這個項目發展成天科合達半導體公司,今年入選國家第三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
截至2020年底,新疆有59家A股上市公司,與陜西一樣多,比重慶還多3家,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排名16居中游,作為一個西北偏遠省份殊為不易。
2011年是中國光伏產業最慘淡的時期,新疆果斷出手抄底,招引東部光伏企業赴疆過冬,與大全能源一同入疆的還有合盛集團、哥蘭德新能源等一批當時的光伏知名企業。
新疆吸引光伏企業有其資源稟賦優勢,新疆煤炭、風能、光能位居全國前列,相應有著較低的電力成本,工業用電價格低于內地價格的50%左右,在電力成本占35%的多晶硅生產上極具競爭力,新疆充足的電力供應能夠保證晶硅低成本生產。
但是青海、內蒙古與西藏等地資源稟賦優勢同樣突出,電價與新疆相差無幾。尤其是青海,除10千伏一般工商業用電,在居民生活用電與其他一般工商業用電價格上比新疆還低,為全國最低價。
中國光伏教父施正榮早在2006年就悄悄在青海布局多晶硅生產,是亞洲硅業的背后實控人。
據經濟參考報2009年報道,當時業界的共識是,綜合太陽能資源、土地資源、氣象、電網、負荷、地理、交通及光伏產業鏈等各種因素,青海省的光伏利用整體條件在全國最優。
青海在2009年發布《青海省太陽能產業發展及推廣應用規劃(2009-2015年)》,其主政官員接受媒體采訪認為,青海成為全國新能源產業老大指日可待。
不過今天來看,光伏產業的老大好像更有新疆味兒。
新疆光伏發電廠 | 圖源:東方IC
既然資源稟賦差不多,產業發展卻結果迥異,倒推產業規劃與執行,新疆或許做得更好。
2010年5月17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隆重舉行。此次會議明確提出,新型工業化是新疆實現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必然路徑選擇,并給予新疆、兵團新型工業化發展一系列的優惠政策。
新疆在2012年發布了《新疆太陽能光伏產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對比青海新疆的產業規劃,新疆對光伏產業認知更深刻,招商思路更清晰。
新疆明確形成“煤—電—硅—太陽能光伏集成應用”循環經濟產業鏈,將資源稟賦優勢充分發揮在光伏產業上游的硅料生產上面,而不是西北其他幾個省份偏向光照優勢注重終端光伏發電。
在缺乏特高壓輸送的前提下,西北省份光伏發電難以做到充分消納。中電投黃河上游公司、中廣核、保利協鑫、無錫尚德集團4家企業曾在西藏山南地區桑日縣建有光伏電站,最后無奈地達成一項看來非常可笑的協議:輪流發電!沒有輪到的電站,只好呆著“曬太陽”。
一般情況下,產業鏈的核心集中在上游原材料、關鍵元器件零部件與下游終端應用兩頭,而一個新興產業的技術標準與終端市場需求處于變動之中,發展之初做強上游更重要。
比如,新疆的產業規劃就在硅料生產方面做了周密測算。
“初步測算,多晶硅材料約占并網光伏發電系統成本的37%,而電力成本又占多晶硅成本的30%以上。若形成1萬噸多晶硅加工產業鏈,就要消耗200萬噸煤炭和近10萬噸的石英巖礦。而1萬噸多晶硅轉化后產品的運輸量僅相當于轉化前資源運輸量的1/200,可極大緩解新疆運輸的“瓶頸”問題,是原子流向電子流轉換、實現由“原字號產品”向高附加值產品發展的一條戰略路徑,對加快實施資源轉換戰略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可以說,新疆的光伏產業成為西部落后地區利用資源優勢結合高科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典型。
康波周期,60年一遇
寧德和新疆兩個案例發生在十年前,它們給了中西部城市一個啟示:
面向新興產業招商,正是中西部城市擺脫梯度轉移的工廠流動風險,快速實現產業鏈升級的可行之道。
當下,科技發展使中西部城市面臨的機遇更多。2021年,兩大經濟規律的周期循環疊加,催生了新興產業爆發。
一是放眼世界,“康波周期”開啟了新一輪循環。
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發現,發達商品經濟中存在長周期變化,一個循環是60年,也就是中國的一個甲子,分為復蘇、繁榮、衰退、蕭條四階段,簡稱康波周期。
最初,康德拉季耶夫以重大經濟危機作為劃分依據,沒有特定的宏觀變量,為此爭議很大。后來“創新理論”鼻祖熊彼特將技術創新作為長波周期劃分的根據,即不同的技術創新與不同的長波周期相互聯系起來,這比重大危機的劃分更加具有說服力。
人類三次工業革命帶來了5次康波周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摩爾定律”接近極限,集成電路發展遇到瓶頸,美國的發展速度變緩的表現,成為本輪長波(第五波)繁榮向衰退轉換的大拐點。
技術創新下的長波周期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熊彼特,雅各布·范杜因,中信建投研發部.
“信息技術爆發期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以美國為主導國展開。當技術從主導國傳導到中國,再擴散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中國作為本輪康波中的追趕人,這個技術在中國還有什么前途可言?”
這是中信建投首席經濟學家周金濤2016年的觀點,他認為一個技術當它在追趕國的滲透程度達到了無孔不入的時候,一定到達了它生命周期的最后階段,這個技術后面就是一個成熟并衰落的趨勢。
的確如此,中國互聯網這些年來的創新乏善可陳,不斷倒騰各種商業模式做流量變現,以至于人民日報連發評論喊話巨頭:
別只惦記著幾捆白菜、幾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創新的星辰大海、未來的無限可能性,其實更令人心潮澎湃。
信息技術增長乏力也讓全球呈現為存量爭奪的內卷狀態,所以我們會看到國際環境的惡化,貿易戰、科技戰接踵而來。
很正常,老大跑不動了,就會伸腿絆老二。
不過新的一頁即將翻開,以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即將到來。
從1958年集成電路問世推動信息革命至今差不多60年,我們正在進入這一輪康波周期的蕭條階段,同時也意味著科技革命的轉折點近在眼前。
圖片來源:硬科技投資的底層邏輯,中科創星.
二是觀察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聯動也開啟了新一輪循環。
過去中國主要是吸收前面幾次康波周期的技術,將其擴散到生產的各個領域,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并不明顯,反而是以房地產、老基建為代表的城市化進程將汽車、家電等技術擴散出去,同時吸收供給過剩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了工業化,實現了經濟增長。
1998年中國啟動房改加快城市化進程,1999年城市化率30.89%,2000年飆升到36.22%,此后逐年上漲,迎來20來年房地產業的高歌猛進,2021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63.89%,城市化進程趨緩,房地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疲軟,進入“建設更好的基礎設施”與“新工業建立”的循環。
城市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的傳動機制
數據來源:邱曉華,“論世界制造業轉移與中國經濟增長”,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2020年,國家提出新基建,加快5G網絡、特高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建設進度。2021年,“十四五”規劃強調諸多科技創新的新工業。
兩個循環進入新的階段,剛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疊加。
于是,我們看到商業模式創新轉向硬核科技創新,互聯網虛擬經濟轉向新工業實體經濟,第四次科技革命呼之欲來,中西部城市的資源稟賦優勢再次顯現。
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動新型制造業西遷
每次科技革命都會帶來新的制造業,點亮城市經濟。
第一次科技革命革新了棉紡織業,讓曼徹斯特成為世界棉都;第二次科技革命帶來的鋼鐵汽車業,崛起了底特律汽車城;第三次科技革命發明了計算機集成電路,讓硅谷成為延續至今的傳奇。
第四次科技革命,表現為碳中和的能源變革與智能化的高端制造業。當前能源變革的制造業屬性大于資源品屬性,所以此次科技革命的核心在前期就是高端制造業。
無論能量還是信息,都需要物質的載體,最終落到實體制造業頭上。
如今硬科技成為熱詞,“硬”字除了代表技術過硬,還有一層硬件制造的含義。
尤其是在科技革命的伊始,更需要搭建硬件平臺,才能在其之上長出軟件生態。哪怕是互聯網,也需要計算機與智能手機作為人機交互的硬件終端。
當移動互聯網進入萬物互聯的AIoT(人工智能物聯網)時代,所需的硬件終端將不再是手機一家獨大。
第三代半導體與新一代模擬芯片制造、新型顯示器件、新型通信基站、XR終端、智能機器人、商業航天、超級高鐵、化學與生物創新藥等等,這些新興產業里其實蘊藏著很多成長中的“頭雁”。
硬科技樹
新能源變革也是棋到中局,接下來的氫能儲能、固態電池等新技術還有很多發展空間。第一次光伏產業爆發,江蘇無錫抓住了尚德電力,后來市場風云變幻,結果光伏產業被新疆抄了底。
只要不是演進到像消費電子與互聯網這種成熟產業,各地都有機會爭搶新興產業的盛宴。
十四五規劃進一步提高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從十三五規劃的15%上升至17%。
相較十三五規劃聚焦的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與材料、新能源領域,十四五規劃新添了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前瞻謀劃未來產業方面,十四五規劃新增了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還將創新驅動發展提升到全新的歷史高度,將科技自立自強發展上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地位。
同時,由于一線城市土地承載有限,成本高昂,上海深圳也在出現新型制造企業溢出現象。
上海整個“十三五”的新增產業用地只有25-30平方公里,2018年特斯拉在上海一次拿地就是0.8平方公里,已經堪稱大手筆。
深圳更捉襟見肘,2018年城市共創大會上王石曾透露,經過四十年的開發,深圳現在可開發的面積只剩下20平方公里左右,每年新增用地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
數據來源:《深圳市城市建設與土地利用“十三五”規劃》
2019年深圳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顯示,2018年深圳有91家規上工業企業出現外遷情況,約占規上工業企業總數的1.1%,累計在深工業總產值599.7億元,占當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1.95%。
報告還指出,近三年外遷的192家企業中,電子信息制造企業共計27家,占全部外遷企業的37.5%。外遷企業已不止是傳統低端制造業,而是延伸至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業。
深圳市總面積1997平方公里,在37個中國城市、副省級城市、特別行政區轄區中倒數第4,還不到蘇州的1/4。
且因為丘陵地形,深圳一半面積被劃入生態紅線保護范圍不得開發。為了力保制造業發展,這些年來深圳在剩下一半土地中堅守工業用地30%紅線,不過這也導致深圳的住宅用地奇缺,造成今天深圳的房價超越北京上海,加重了制造業的用地成本,產生擠出效應。
2020年10月,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宣告解散,其稱深圳工廠租期將于2021年到期,但因當地租金漲的過高,為了節省運營成本,所以不得不關閉深圳工廠。
深圳的企業搬遷潮并非現在才出現。早在2016年,時任深圳市長許勤就曾在講話中表示,“近期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
據科技部對國家高新區的2020年綜合排名,深圳高新區僅次于北京、上海,但在可持續發展能力這一項排名第十,在成都、蘇州、合肥等城市以后。
新型制造業爆發和一線城市的有限承載正在賦予中西部城市招商引資新的歷史機遇。
中西部產業升級,從招引到招投
新型制造業西遷,與上一輪成熟制造業西遷,又不一樣。
后者只看中成本優勢,哪的地和勞動力便宜,就往哪里去。前者除了成本優勢,還對當地人才供給、居住環境等提出了要求。
因為新型制造業不是簡單的來料加工組裝,研發制造一體化,制造工藝精細化,都需要高技術人才來執行。
梳理下來,中西部城市主要是成都、重慶、武漢、鄭州、西安、貴陽等地具備的綜合優勢較為明顯。
成都位于平原,環境宜居,有電子科大、川大、西南財大輸送人才。重慶是西部之頭、中部之尾,重工業發達。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還印發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繼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之后,確定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重大戰略地位。
武漢九省通衢,云集武大、華中科大、中南財經等高等院校。鄭州占據交通樞紐,經濟腹地廣,近年發展很快。西安千年古都,西工大坐鎮科研基礎。貴陽敢為天下先,前幾年大數據產業搞得風風火火。
總的來說,中西部城市各方面資源稟賦差距不大,誰能抓住新型制造業西遷的機會長出龍頭企業,關鍵還是看企業招引能力。
地方政府招商,最早是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吸引企業,有了產業基礎之后發展到產業鏈招商,逐步將龍頭企業招引進來,帶來配套企業形成產業集群,進入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這是針對成熟產業的招商套路。
新興產業的產業鏈既不完善,也沒有明確的龍頭企業,無論是寧德時代還是大全能源,都不是產業鏈招商帶來的成果。
它們的共同點,都是本土資源與高科技結合的產物。
盡管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寧德的老鄉資源,或者新疆得天獨厚的煤電土地與光照資源,要將新興產業的潛在頭雁企業引來,通行辦法之一是砸錢。
新興產業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是個企業都缺錢,從產業鏈招商到資本招商,各地政府成立創投基金,從招引到招投正在成為新的趨勢。
既要招大引強,爭搶蛋糕;也要招精引新、投新做精,做大蛋糕。
中西部城市擺脫“廠妹”的宿命,在此一舉。
資料參考:
[1] 《濤動周期論》,周金濤.
[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太陽能光伏產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
[3]《創新:不滅的火炬——科技與產業鏈發展研究報告》,中金公司.
[4]《硬科技投資的底層邏輯》,中科創星,米磊.
——END——

高陽
<rt id="8euwm"></rt>
<rt id="8euwm"></rt>
<li id="8euwm"></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