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原文標題:論“血流漂杵”的歷史真相如涉版權(quán)請加編輯微信iwish89聯(lián)系哲學園鳴謝相關(guān)鏈接【精彩爆文】點擊藍字周滅商:血腥代理人、神秘運算術(shù)、牧野鷹揚…作者:白立超(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講
原載:《西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原文標題:論“血流漂杵”的歷史真相
如涉版權(quán)請加編輯微信iwish89聯(lián)系
哲學園鳴謝
相關(guān)鏈接【精彩爆文】點擊藍字
周滅商:血腥代理人、神秘運算術(shù)、牧野鷹揚…
作者:白立超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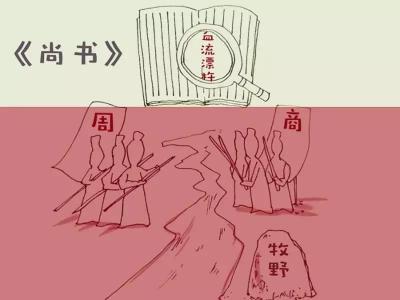
摘要:《尚書·武成》記載牧野之戰(zhàn)“血流漂杵”。由于此條記載的殘酷性、反常識性,同時也與儒者對周制的推崇格格不入,所以歷代學者多以考證的方法試圖彌合。學者將精力更多集中在對“杵”的考證上,也有從“漂”字入手者,皆在試圖找尋這一場景的合理性以及與周制的融洽性,但始終未能解決。事實上,牧野之戰(zhàn)與商周時期的特定氣候相關(guān),與一場持續(xù)性的暴雨相關(guān),也與周人臨河布陣相關(guān),最終才出現(xiàn)“血流漂杵”的特殊場景。廓清這一問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歷史真實與思想價值之間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牧野之戰(zhàn);血流漂杵;真相
一、“血流漂杵”的理解困境
牧野之戰(zhàn)標志著周族經(jīng)過長期努力終于完成了滅商大業(yè),建立了新的天下秩序。但由于時代 久遠,典籍散佚,牧野之戰(zhàn)的諸多細節(jié),早已消失在歷史深處,成為一樁謎案。歷代思想家由于立場不同、資料選擇各異,雖不斷對“血流漂杵”進行解說與重構(gòu),卻未能厘清其真實性。所以筆者擬在已有學術(shù)成果的基礎(chǔ)上,努力尋找“血流漂杵”的特定歷史真實。
據(jù)現(xiàn)存典籍的只言片語,我們對牧野之戰(zhàn)有一個輪廓式的了解。關(guān)于雙方投入的作戰(zhàn)兵力及其規(guī)模,《詩經(jīng)·大明》中有“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的描述,《逸周書·克殷解》也有“周車三百五十乘陣于牧野”[1](P339)的記載;關(guān)于雙方的戰(zhàn)術(shù)布置,《逸周書·克殷解》有“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1](P341)的簡略記載;關(guān)于此戰(zhàn)的激烈程度,《尚書·武成》僅以“血流漂杵”[1]一筆帶過。
但由于商周變革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意義,因此關(guān)于這場戰(zhàn)爭慘烈程度的爭論在先秦時期已經(jīng)開始。孟子率先質(zhì)疑“血流漂杵”的記載,并由此發(fā)出“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感慨,開啟了后世對“血流漂杵”記載與解釋的種種爭議。
筆者認為此條記載引發(fā)關(guān)注與討論最重要的原因,是儒家學者有意為周武王回護,因為這條史料的解讀,涉及商周革命史事真實性與政治正當性的沖突,尤其是儒家學說在傳統(tǒng)社會中長期居于主導地位,如何評價湯武革命、文武之德,都是非常重要的學術(shù)和政治問題。但此條記載的反常識性也不可忽視,因為在我們正常接受的范圍內(nèi),即使戰(zhàn)爭非常殘酷和血腥,史書有“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shù),軍至漸臺,血流沒趾”[2](P346)等記載,然“血流漂杵”的現(xiàn)象,似乎很難發(fā)生。
正因如此,東漢王充從事實角度質(zhì)疑“血流漂杵”,他認為:“《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糧,或作干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2](P391)
勿庸置疑,王充這一質(zhì)疑,為相信“血流漂杵”真實性的學者提出了最難解決的問題,因此學者多以過辭、虛言稱之。如魏了翁在《尚書要義》中指出:“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fā)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眾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自攻于后以北走,自攻其后,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起血流漂杵,是言不實也。”[3](卷10)
因此圍繞“血流漂杵”到底是真實發(fā)生還是過辭、虛言的爭論,引發(fā)了諸多討論。歷代學者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雖動機不同,但研究徑路卻出奇一致,即從小學角度進行考釋,并幾乎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對“杵”字的考證上,以求“血流漂杵”場景合理。
二、“血流漂杵”的考證困境
在“血流漂杵”四字中,歷代學者最關(guān)注“杵”的考證,個別學者也會關(guān)注“漂”的理解。
(一)“杵”的考證
“杵”為何物?軍隊中為何會出現(xiàn)此物?此物又在何種情境下能“漂”(漂浮)?這是學者必須解決的問題。傳統(tǒng)訓詁學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 “杵”是兵器“大盾”。一種認為“杵”當為古“樐”字,其他典籍中也作“鹵”“櫓”“鹵”。此說法被一些學者接受,因為在典籍中有用例,這方面論述最詳盡的是清代學者黃生的《義府》:“《周書》‘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作漂鹵,陳琳《檄文》作漂樐,樐,大盾也。二語皆本《周書》,以理推之,樐者,軍中所宜有,杵非軍中所宜有也,予因悟杵即古樐字,蓋古杵字本單作午,加木為大盾之杵,諧午聲,后借午,為午未之午,又借杵,為舂杵之杵,因續(xù)制樐字以代之,惟《周書》尚作杵,蓋舂杵亦器用之之類。注家依此作解,所以存而不易,若賈、陳作鹵、樐,是尚知杵即樐字耳。”[4](卷上)
另一種認為“杵”當為“桿”的誤寫,“櫓”為“桿”的別稱,據(jù)《說郛》載:“《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云:‘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為桿字之誤也。案:《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郄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為汗,桿一名楯,一名櫓,櫓即桿,俗稱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5](卷6上)
2.“杵”是兵營中筑壘壁的工具。“杵”與“版”一起,均為筑土墻的用具。“杵”主要是用于搗土,使土更堅實。據(jù)《廣雅·釋器》載:“筑謂之杵。”
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引用鄭玄《周官·鄉(xiāng)師》注引《司馬法》的材料:“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筑。”[6](P261)以此證明周軍軍營中可能會出現(xiàn)此物。惠士齊將此說完善:“鍬鍤筑者,杵頭鐵沓也,以筑壘壁,故《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語,孟子以為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血流漂櫓,而《益壤篇》又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逐鹿之野,血流漂桿,秦至無道,曓于帝辛,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于黃帝,筑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臿,趙魏之間謂之鍬,東齊謂之梩……”[7](卷3)
3.“杵”是“舂杵”。“舂杵”即舂米器具,典籍中經(jīng)常“杵臼”連用,是軍營后勤用具。此說為趙岐、孔穎達、孫奭、朱熹等學者所接受,可以說代表了經(jīng)學的正統(tǒng)解釋。在部分典籍中,“血流漂杵”就有另外一種說法,正是“血流舂杵”:
言武王誅紂,戰(zhàn)斗殺人,血流舂杵。[8](P2773)
自攻其后,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9](P185)
上引材料甚至又反過來成為“杵臼”的例證。如《太平御覽》卷762中“杵臼”一項列舉典籍中作為舂米之具“杵”的材料多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將《尚書》《孟子》“血流漂杵”和“血之流杵”兩項列入。后世學者注釋《尚書》時也經(jīng)常引用:“朱子孟注,杵,舂杵也。兵間安得有?舂杵,曰此兵間所宜用也,凡古人行兵,人各攜畚、鍤、版、杵之屬為營塹備,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為羅爂以為鍋。”[10](卷9)可見此觀點之影響深遠。
(二)“漂”的理解
1.漂浮說
通過對“杵”的考證可以發(fā)現(xiàn),學者對“杵”所指物品的爭論與考證,目的就是要使得這一物品在“血流”中“漂浮”得以可能。但無論如何,這終究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才會出現(xiàn)以上的種種異說。學者討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杵”可以“漂”,同時在戰(zhàn)場可能出現(xiàn)。所以釋“漂”為“漂浮”就是以上種種說法的默認前提,我們姑且稱之為“漂浮說”。
2. 飄濺說
“漂浮說”最大的問題就在于“杵”的體積和質(zhì)量都不足以漂浮在血流之中,所以王夫之發(fā)現(xiàn)了“漂浮說”解釋的困境。
在《尚書稗疏》中,王夫之首先肯定了“杵”當為“櫓”,也就是大盾。而對“漂”的解釋卻另辟蹊徑,試圖沖破傳統(tǒng)解釋的困境,他指出:“漂杵本或作鹵,楯也。軍中無杵臼之用,當以漂櫓為正。杵字從午得聲,古或與鹵通,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之說太不經(jīng),雖億萬人之血亦必散灑于億萬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11](P128-129)
明確指出“漂浮說”最根本的問題亦即不為人所信的原因就是:“雖億萬人之血亦必散灑于億萬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認為這里的“漂”應當取“飄濺”之義,“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實際上是說“漂”在此可以通假為“飄”,是血濺出而在空中飄,這樣血就飄濺到大盾上。通過這樣訓詁的方式,王夫之將“血流漂杵”的記載重新解釋為戰(zhàn)爭中常見的一個場景,于是“血流漂杵”既不影響周武王之德,又肯定了經(jīng)書《尚書》的記載為實錄。
王夫之的說法突破了傳統(tǒng)的思維定勢,以“漂”字為切入點,給“血流漂杵”一個較為完備的解釋,從文字學上解決了“血流漂杵”的現(xiàn)實可能性問題。載入史冊的“血流漂杵”會是這樣一個如王夫之所理解的非常普通的情景嗎?這是十分可疑的。
《哈佛中國史》
三、“血流漂杵”的特殊場景
無論學者怎樣考證“杵”,默認的前提就是既要在軍營中出現(xiàn),又能夠漂浮或者飄濺其上。從上引諸解可以看出,傳統(tǒng)小學對“血流漂杵”的考證,始終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認為,以往學者的討論都太過糾纏于“血流漂杵”這條記載的普遍性、常識性意義而忽略了歷史記載的特殊性。特定的史實只有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才是合理的,離開了特定場景,歷史展現(xiàn)給人們的可能就是另一種狀況。對“血流漂杵”的研究,也應當鉤沉史料,試圖接近歷史場景。在儒家思想主導的傳統(tǒng)社會中,但凡討論“血流漂杵”都與周武王的形象相關(guān),所以我們選用與“血流漂杵”相關(guān)的史料時,應當與稱頌周武王之德立場的材料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就是說我們選用的史料本身可能與牧野之戰(zhàn)場面描述的相關(guān)性不大,卻對于接近歷史場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如前所述,王充最先通過場景復原的方式否認了“血流漂杵”記載,而筆者根據(jù)史料記載以及近現(xiàn)代以來學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擬從天氣狀況、具體地望和氣候條件三個方面來論述牧野之戰(zhàn)的特殊歷史場景。
(一)牧野之戰(zhàn)與一場持續(xù)性暴雨相關(guān)
牧野之戰(zhàn)與持續(xù)性暴雨的關(guān)系,史籍記載甚多。這些史載雖出于不同目的,試圖說明不同的問題,但在不經(jīng)意間都提到了牧野之戰(zhàn)中天氣狀況的特殊性: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12](P123-126)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13](P388)
武王東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佑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14](P109)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軛折為三者,君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15](P94)
《荀子》《淮南子》《史記》中也有類似記載。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一般不為學者所注意的材料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一種特殊天氣現(xiàn)象,那就是“雨”“暴雨”“雨不休”等。其中一些記載也曾被吸收到《尚書》注疏中。有學者對“待天休命”的解釋,也與降雨聯(lián)系起來以示“天命”:
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16](卷23)
孔傳: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疏云,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陣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韋昭云,雨者,天地人和同之應也。蔡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10](卷9)
筆者認為這些敘述是可信的,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材料并未經(jīng)過儒者太多加工,甚至是作為術(shù)數(shù)類、陰陽家的材料被保留下來,長期并未受到重視,也未遭到改造,所以真實性反而比較高。正是這些無意于價值重構(gòu)的邊角料,卻為解決歷史中一些難題提供了重要線索。正如葛兆光所言:“文獻中間也有很多被遺棄的邊角資料,之所以被遺棄,是因為它無法按照傳統(tǒng)的歷史觀念被安置在歷史敘述的某個部位……如果歷史敘述的觀念有所變化,可能這些‘邊角廢料’就會突然身價百倍。”[17]
這些指向“雨”“暴雨”邊角料,為還原牧野之戰(zhàn)的場景提供了可能,同時也回應了千年之前王充對“武王伐紂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的質(zhì)疑。
雖然“血流”已經(jīng)不是問題,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即使不會發(fā)生“兵頓血流,輒燥入土”的情形,何以“血流漂杵”呢?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戰(zhàn)場呢?
我們知道,“牧野”是一片大平原,史料記載牧野之戰(zhàn)“周車三百五十乘陣于牧野”。戰(zhàn)車能夠順利奔馳的地方,必定地勢相對平坦,據(jù)《逸周書》載,牧野之戰(zhàn)周軍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就是周武王“以虎賁戎車馳商師”,最終導致商軍陣腳大亂,繼而大敗。在相對比較平坦的地勢中,沒有洼地之類的地形,即使是暴雨、“雨不休”,“血流漂杵”場景出現(xiàn)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其實牧野之戰(zhàn)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河流。商周軍隊布陣于河流旁邊,“血流漂杵”的特殊場景肯定會出現(xiàn)。
(二) 牧野之戰(zhàn)中商周的陣線一翼為河流
牧野之戰(zhàn)的地望研究,歷來爭議較大,主要有朝歌南說,汲縣說,新鄉(xiāng)牧村說[18],大體位置基本圍繞在殷墟安陽附近。近年來學者通過史料考證、實地調(diào)查、考古發(fā)現(xiàn)、地名傳說辨析等方法,更多地認同新鄉(xiāng)牧野說。這三種說法并沒有根本矛盾,只是大地名與小地名的關(guān)系,筆者認為新鄉(xiāng)牧野是牧野之戰(zhàn)發(fā)生最具體、最確切的地理位置。學者通過實地勘察和資料爬梳,逐漸確立了牧野之戰(zhàn)戰(zhàn)場大體位置,并且明確指出“商周軍隊決戰(zhàn)之前所列陣線,其南段均以清水為其一翼之屏障”[18]的具體列陣方式。這里提及的清水位于太行山東麓,是古黃河的重要支流之一,當時水量比較大。
那為什么周武王會選擇布陣于河流旁邊呢?牧野之戰(zhàn)是一次以少勝多的戰(zhàn)役,從軍隊數(shù)量上來看,周族沒有任何優(yōu)勢。在此情況下,周軍主動出擊,以逸待勞,率先抵達戰(zhàn)場,以河流為側(cè)翼進行布陣,河流成為軍陣的一道天然防御屏障,對己方非常有利。
從軍事學的角度來看,在兵力相對處于弱勢的情況下,以河流為軍陣一翼以穩(wěn)固軍陣是非常重要的方式。而且在后來歷史發(fā)展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佐證,如許多改變歷史進程的重大戰(zhàn)役莫不與河流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如決定楚漢之爭根本局勢轉(zhuǎn)變的濰水之戰(zhàn),奠定三國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戰(zhàn),導致南北分裂繼續(xù)得以維持的淝水之戰(zhàn),決定明清鼎革的薩爾滸之戰(zhàn)等,均與大江大河密切相關(guān),也多是以少勝多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
(三)牧野之戰(zhàn)的時間確認與釋疑
至此,牧野之戰(zhàn)“血流漂杵”場景的出現(xiàn),從特殊天氣、特定地望上來說,似乎已經(jīng)很明朗了。但還必須補充論證大戰(zhàn)具體時間,因為在史料搜集中遇到了這樣一條:“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19](P823)
根據(jù)《國語·周語下》“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的記載可以看出,牧野之戰(zhàn)發(fā)生在周歷二月,換算成夏歷就是十二月,其所處的月份有可能是公歷的12月、1月或2月,這是一年四季中的冬季。
根據(jù)“夏商周斷代工程”對牧野之戰(zhàn)時間的確定,如江曉原、鈕衛(wèi)星推算的日期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劉次沅、周曉陸推斷的日期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雖年日有差異,但月份都在1月。牧野地區(qū)的1月的氣溫是什么情況呢?從今天的氣候條件來看,安陽地區(qū)1月的平均氣溫低于攝氏零度,若有降水,只能是雪。典籍中記載的雨、雪哪個更可靠呢?若當時氣溫低于攝氏零度,清水流域一定會結(jié)冰。若以今天該地區(qū)的氣候狀況進行衡量,絕不會出現(xiàn)“血流漂杵”的現(xiàn)象。歷史上會出現(xiàn)嗎?這里牽涉歷史上氣候變化的問題。
究以氣象遷變,歷史上安陽的氣溫是有所變化的。竺可楨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指出:“可以說,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qū)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20]并根據(jù)物候進一步指出,這種溫暖的亞熱帶氣候一直持續(xù)到公元前10世紀左右。在牧野之戰(zhàn)發(fā)生的時間區(qū)間,安陽地區(qū)的氣候?qū)儆趤啛釒夂?全年不結(jié)冰,降水形態(tài)不可能為雪而只能是雨,而且清水流域也不會結(jié)冰或積雪。據(jù)此可見“武王伐紂,雪深丈余”的記載肯定有誤,或許出于后世學者根據(jù)已經(jīng)轉(zhuǎn)入寒冷期的氣候現(xiàn)象對歷史的想象。
結(jié)合以上三個非常特殊的歷史因素,筆者認為,“血流漂杵”是對在特定的天氣狀況(大雨天)、特定的地點(牧野清水河岸)、特定的時間(尚處于亞熱帶氣候的周歷二月)發(fā)生的一次重大戰(zhàn)爭的一個側(cè)面的重要描述。
牧野之戰(zhàn)的真實場景可能是:商周大軍雨中大戰(zhàn),嘈雜的戰(zhàn)場上,鮮血與雨水混成一片,在士兵的腳下,不斷流淌。大雨將血水沖入清水河中,整個清水河水變成血水,并且在河面上漂浮著士兵丟棄的木盾牌。所以“血流漂杵”只是在特定的天氣狀況、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氣候條件下發(fā)生的特殊事件,不具有普遍性。
當然在這樣的場景之下,無論是“杵”被釋為大盾、舂杵、還是筑壘工具等都無礙于理解,而筆者認為“杵”被釋為大盾,更符合歷史實際,因為從《詩經(jīng)》還是從漢代引用的異體字情況來看都比較清楚。后世之所以會出現(xiàn)種種異說,主要還在于對特殊歷史場景不了解,又急于對周武王形象進行回護所造成的.
四、余論
數(shù)千年間,“血流漂杵”的看似反常識的場景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讀解,“血流漂杵”歷史真實性長期被思想家遮蔽或曲解。在現(xiàn)代史學觀念下,對歷史真實的發(fā)掘是史學家孜孜不倦追求的一個目標。
筆者認為,“血流漂杵”發(fā)生在特定的時空中,在失去了這個特殊場景之后,學者若從普遍性思維入手,必然會導致種種異說或曲解。但歷史上的異說或曲解依然有其價值,如儒者通過對“血流漂杵”的解讀,表達了他們對歷史哲學的建構(gòu),寄托了他們的善治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血流漂杵”在傳統(tǒng)經(jīng)學、史學和子學中僅僅是一個符號,是一個忘卻了歷史之真的符號,正是對這樣一個符號的種種爭議,體現(xiàn)出了傳統(tǒng)時期的歷史哲學和價值取向的某些方面。
《哈佛中國史》
參考文獻: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 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
[3] 魏了翁.尚書要義[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黃生.義府[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陶宗儀.說郛[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 王念孫.廣雅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 惠士奇.禮說[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 趙岐,孫奭.孟子注疏[M]∥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9] 孔安國,孔穎達.尚書正義[M]∥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10] 朱鶴齡.尚書埤傳[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王夫之.尚書稗疏[M].長沙:岳麓書社1988.
[12]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2.
[13]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4] 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5] 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6] 陳經(jīng).陳氏尚書詳解[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J].讀書,2003,(1).
[18] 蘇德榮.談牧野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地望[J].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5).
[19] 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0]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中國科學,1973,(2).
注釋:
[1]雖然傳世《武成》篇屬古文《尚書》,但根據(jù)先秦兩漢典籍直接或者間接引《尚書》材料來看,此條材料本身是可靠的,參見陳根雄、何志華編著《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匯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177-17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