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媽媽喜歡的是女生嗎?”黃惠偵坐在攝像機后,把這個壓在心底將近四十年的問題拋給三舅。“我不知道。”三舅的否認幾乎脫口而出。他舉起右手撓撓頭,隨后又放下。在心理學上,人們常把這樣的動作視為緊張或說謊的佐證。“知道這也沒用——你知道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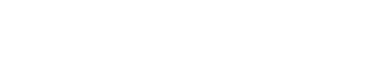
“你知道我媽媽喜歡的是女生嗎?”
黃惠偵坐在攝像機后,把這個壓在心底將近四十年的問題拋給三舅。
“我不知道。”三舅的否認幾乎脫口而出。他舉起右手撓撓頭,隨后又放下。在心理學上,人們常把這樣的動作視為緊張或說謊的佐證。
“知道這也沒用——你知道這些要做什么?”他長嘆一口氣,避開鏡頭向外張望,隨即岔開了話題,“廟會頭陣(臺灣一種民間祭祀)快來了”。
黃惠偵已經不止一次看到類似的反應,面對同樣的問題,二舅把“不知道”連說了兩次,大姨則表示“我要去洗衣服了”,然后顫巍巍撐起身,逃離鏡頭的凝視。
見證這一切的黃惠偵開始“分裂”:作為女兒,她的第一反應是“你們怎么能睜眼說瞎話,明明你們都知道我媽媽喜歡女生”;而導演身份的那個她又覺得,“他們的反應是在是太好了”,觀眾看到這里一定會產生荒謬感,這讓影片更有力量。
“我們家有人知道嗎?”她向二舅最后一次確認。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換來一陣沉默。
“那你現在知道怎么那么冷靜,完全都不驚訝?”
“……沒什么好驚訝的。”一段更長時間的沉默。
逃避,是黃惠偵在拍攝紀錄片《日常對話》時經常要面對的情況,而這部片子的主題,則關于她那個喜歡同性的母親。2014年,當她第一次認真地告訴母親她在做這件事時,母親的第一反應是,“有什么好拍的,誰要來看啊?”
但不管有沒有人要看,為了拍攝這部片子,黃惠偵和母親在時隔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了臺灣中南部云林縣鄉下的老家。
探親的幾天里,當舅舅姨媽忙著回避“媽媽是否喜歡女生”這類問題時,母親和她的女朋友,或許正在廚房為全家人做飯。
戲劇沖突始終在電影中存在。一方面是母親的兄弟姐妹們對母親身份的諱莫如深,另一方面,在鏡頭記錄下的畫面里,舅舅、姨媽與母親和她的女朋友,在同一個屋檐下,相處融洽。
2017年,這部被母親說成“誰都不要看”的《日常對話》,獲得柏林電影節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當年在臺灣拿下400多萬新臺幣的票房,并代表臺灣參選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今年40歲的導演黃惠偵,一個沒有念完小學的全職媽媽、社會運動工作者,用了18年時間,將母親一生的故事梳理進87分鐘的影像,呈現在世人面前。
在柏林影展的頒獎禮上,黃惠偵捧著獎杯說:“這個獎是我能帶回去送給我媽、以及在臺灣此刻仍為婚姻平權努力著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禮物。”
這是一個關于我母親的故事。她出身在一個傳統的年代,但卻是個很不傳統的女性。她是擔任“牽亡陣”紅頭法師的女同志,興趣是抽煙、打牌,還有收集檳榔盒上的清涼美女圖。
七歲那年的我發現媽媽喜歡的是女人,現在妹妹七歲的女兒問我:“阿姨,外婆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呀?”
這個答案很長,于是我只好拍一部片來回答她。
這是黃惠偵為電影寫下的第一段故事大綱,但她想講的,并不僅僅是一個同性愛情的故事。 “我和媽媽的故事,不只是因為我們運氣不好,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這既是一個家庭的私事,也關乎整個社會。
正如她后來又為母親寫了一本書,書名叫《遲來的告白》,黃惠偵想說的是,“我們該如何向我們的家人表達,尤其是表達愛。”
01 我的媽媽,喜歡女人
黃惠偵的母親——洪月女,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阿女。
1956年,阿女出生在臺灣南部的農村,是家中第五個孩子。整個家庭都是務農,幾分地種水稻、種玉米、種花生,收入極少,只夠勉強養活孩子。
重男輕女的年代,讀書的機會輪不到女孩們,阿女的書只念到小學。70年代是臺灣紡織業的興盛時期,14歲的阿女去了臺北的紡織廠當學徒。剛到城市,她常躲在棉被里哭,偷跑回家又會被勸回臺北,因為家人說在鄉下沒有出路,年輕人不該留在那里。
21歲阿女結婚,22歲生下黃惠偵,24歲生下妹妹黃惠娟。丈夫是隔壁縣刷油漆的臨時工,經親戚介紹認識的。他嗜賭,家暴,把阿女賺的辛苦錢揮霍一空。
32歲逃離家庭,帶著兩個女兒做“牽亡陣”謀生,這是一份被許多人看不起的工作。“牽亡歌陣”是一種臺灣民間喪葬儀式,做一些超度亡靈的法事和戲曲,在80年代很盛行,但也常被認為是封建迷信。
阿女買過房子,又賣掉還債,經濟短暫寬裕過,但長期處于窘迫,現在與黃惠偵及其外孫女同住。
這便是阿女大半生的履歷,微不足道,少有彩色。
阿女的一生中有十幾個女朋友,這可能是她人生履歷中為數不多可以笑著說出來的事。她的個頭不高,眼睛不大,鼻梁也不那么挺,但總能交到能說會唱的漂亮女友。
初戀是19歲在臺北當紡織女工時認識的。70年代的臺灣,露天演出的歌仔戲班遍布街頭,阿女下工后到附近的戲臺看戲,與臺上演俊美小生的演員暗生情愫。
她們相愛、同居、爭吵,一年半后分手。一氣之下,阿女順從家里的意愿,嫁給了黃惠偵的父親——那個在結婚前只見過一面的男人,由此開始人生的厄運。多年以后,阿女和初戀重新聯系,才知道彼此的婚姻都很不順遂。
在黃惠偵的記憶里,大概不到10歲的時候,她第一次見到母親帶女朋友回家。那時阿女組起了自己的“牽亡陣”團隊,女朋友叫小春,算是阿女的員工。
再后來,黃惠偵又陸續認識了娜娜、麗麗、雙雙……以及更多她不知道名字的阿姨們。
“從小看著我媽不間斷地重復著喜歡某人、追求某人,最后告別某人的輪回,不得不佩服她實在比我積極勇敢得多。”
小時候,黃惠偵并不覺得母親喜歡女人有什么不對,直到11歲那年,有長輩告訴她說,你媽媽是同性戀,是“不正常“的。偏見和歧視,這讓黃惠偵在此后很長時間內怨恨,為什么母親要和別人“不一樣”。
但讓黃惠偵更加恨的是,為什么母親愛她的女朋友們,總是勝過愛她的女兒們。
在女朋友眼中,阿女充滿著無限的柔情:嘴甜、輕聲細語,體貼溫柔,出手大方,甚至樂于幫女友洗內褲……
“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正常女人,都是因為遇見你媽,才被愛情沖昏頭。”即便分手很久后,女朋友當著黃惠偵的面回憶起阿女,依然露出少女般的神情。
黃惠偵在《遲來的告白》里不禁感慨寫下,“對我媽來說,愛人就是要捧在手心上,讓她覺得自己是整個宇宙里唯一的一朵玫瑰花,獨特且備受寵愛;直到有一天,這朵宇宙里唯一的玫瑰,發現還有另一個宇宙與另外一朵玫瑰花存在。”
這也是一種從未在黃惠偵面前表露過的柔情。“雖然我們已經一起生活三十幾年,但我們卻一直都好像是陌生人一樣。除了桌上的飯菜,我跟她的生活可以說是完全沒交集。”
不知為何,阿女甚至會在外人面前將親生女兒抹去。她曾向女朋友這樣訴說自己的過往:結過婚,一個禮拜后就離婚了,只和丈夫同床一次,兩個女兒是領養來的。
“我的媽媽,究竟愛我嗎?”這句對多數人來說毫無疑問的肯定句,在黃惠偵心底,長久以來一直是個疑問句。
于是,《日常對話》成為一封寫給母親的書信,代替她問出這個問題。
02 父親,無處不在的幽靈
在這封信里,黃惠偵故意將父親隱去了。“如果把父親放進電影中,我母親沒辦法接受。”
那是一個阿女永遠都不會原諒的人。
他叫阿源,比阿女大5歲,客家人。皮膚黝黑,濃眉大眼,塌鼻梁,身上混雜著汗水、油垢、煙酒和檳榔的難聞氣味。
阿女相親時第一眼見他就沒好印象,“一臉橫肉,目光兇狠,不像是個好人”。但在阿女母親極力撮合下,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她就已經成為了阿源的妻子。
婚后,阿女跟著阿源來到臺北,住進不到15平米的出租公寓,用薄木板分隔出兩間房,分別放著一張單人床和一張雙人木板床,廁所和廚房與其他租戶公用。兩個女兒陸續出生,一家四口和所有家當,都擠在這個簡陋的家中。10歲以前,黃惠偵一直住在這里。
阿源是個油漆工,和其他底層建筑工人一樣,都是做一日工、領一日工資。他實在算不上一個合格的丈夫和父親,好吃懶做、酗酒,賺來的錢從不進家門,全部都交給賭場和煙酒攤,還搜刮母女做牽亡陣賺來的錢去賭博,不給就是一頓打。
咚咚碰,父親用腳踹著母親。
噼噼啪,父親扇著母親巴掌。
嘶嘶唰,父親扯著母親的頭發。
黃惠偵至今清晰地記得,每一次家暴中不同的聲音意味著什么。
但母親總是靜默的,任憑怎樣的疼痛,她也決不求饒,這反而激起父親更大的怒火。沒有人知道,阿源是否覺察阿女喜歡女人。
“你有沒有去問過要怎樣才能離婚?”
“有問過,但是我覺得那樣很丟臉。”
“你覺得讓人家知道你被家暴很丟臉?”
“對啊,為什么長那么大還要被人打?”
終于,在結婚十年后某一個普通的下午,趁著阿源外出干活,阿女翻遍家中尚未被阿源搜到的財物,帶上兩個女兒,走出家門,走下樓梯,走到外面攔下一輛出租車。看起來就像一位母親帶著年幼的女兒出游,那樣地平淡無奇,但卻是一條再也不回頭的路。
后來,聽說阿源經常到各處牽亡陣現場打聽母女的下落,身上一定會帶著用報紙包住的刀。
離家后兩三年,黃惠偵見過父親一次。她隨牽亡團演出,一次出陣時,棚架搭在一個籃球場內,她正燒著金紙,恍惚間用眼角余光瞥見,籃球場外站著一個人,那正是父親,他的視線正投向黃惠偵。
父親的表情看起來激動又疑惑,也許是因為臉上畫著妝、穿著演出服,他沒能完全確定眼前的女孩是自己離家的女兒。
黃惠偵的雙腳幾乎癱軟下來。她迅速走進棚內,一直躲到儀式結束。再往外面看一眼,父親已經不見。
“人活著總是需要點什么去支撐或驅動生命,不管那是愛,或是恨,都行。我不知道父親那天看見了什么,或想通了什么,讓他決定放棄找尋我們。但不管是什么,我想都不是讓他好過的東西,因為,那讓他最終失去了活下去的動力。”
考慮到母親的情緒,黃惠偵并沒有把阿源的形象放進《日常對話》中。
“我到現在都很氣,那種人死掉最好,留在世上造孽。如果殺人無罪,我第一個就要殺他。”鏡頭前的阿女向來惜字如金,但談及丈夫,她不惜說出最激烈的言語。
具體的父親形象不存在,但“父親”又是電影中無處不在的幽靈。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人長大就是要嫁人,不然要做什么”,黃惠偵的舅舅和姨媽,這樣解釋為什么要把妹妹嫁給一個只見過一次的男人。
當他們得知妹妹經常被這個男人打罵,能做的也只是和阿源說“打狗也要看主人,你要罵她也等我不在的時候再罵。”
阿女也有著同樣暴力的父親,和默默承受一切的母親。
“外婆為什么要自殺?”黃惠偵問。
“因為你外公也很會罵人。她就是被罵到受不了,才會想自殺。”
這不僅僅只是阿女的夢魘。阿女有很多唱歌仔戲的朋友,她們有的是俊俏的小生,有的是嬌美的苦旦,但不管在戲臺上扮演什么角色,下了戲之后,她們就都變回別人的老婆。
而每當她們出現在阿女家中,身上總是會帶著顏色深淺、面積大小不同的淤青傷痕。阿女一直都用一罐“金門一條根”藥膏,為她們擦拭傷口。
在《日常對話》的世界里,鏡頭里的都是女性,但在鏡頭外,她們無時無刻不被“父親”的幽靈籠罩。
“這個世界上的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從小到大,這是阿女對兩個女兒唯一耳提面命的囑咐。
十多年后,黃惠偵母女最終聽到阿源上吊自殺的消息。消息是阿源的弟弟帶來的,因為他墊付了喪葬費,需要母親這個名義上的妻子取出阿源的勞保,來償還費用。
黃惠偵代替母親最后去看望了父親。骨灰放在最上一層,因為這個位置的價格最便宜。“活在世上的時候處在底層,過世以后位置變高了,但一樣都是邊緣。”對于父親的一生,黃惠偵這樣總結。
03 等待,一次傾訴的機會
黃惠偵心中有一個藏了三十多年的秘密,她一直想質問母親,卻不知該如何訴說。
始作俑者依然是那個幽靈:在那個尚未逃離的家中,幼年的黃惠偵曾被父親猥褻。
她一直覺得,母親知道這個秘密,但仿佛當作什么都沒發生。因此,她恨她的母親。
“那個秘密讓我無法愛自己,也無法全然無疑地去愛我媽。”黃惠偵在《遲來的告白》中寫道,她恨的從來都不是因為父親做了什么,而是來自于母親的不問。
一張餐桌,母女對坐,這段秘密終將被解開。
這是《日常對話》中最重要的一個場景,也是紀錄片拍攝的最后一個場景。在一起生活了半輩子,黃惠偵終于借著“拍電影”的理由,與母親第一次面對面敞開心扉。
“我一直以為是因為這件事,所以你很討厭我,不愿把你心里的事告訴我。”黃惠偵哭著對母親說。
但阿女連連否認,她不知道這件事,更不會因此討厭女兒。阿女一只腳踩在椅子上,用這個姿勢把頭深埋進胸前,沉默著。
“你講這些事讓我更生氣。”末了,面對女兒的傾訴,她幽幽地說。
黃惠偵原以為母親是在氣她,氣她對她的誤解。但后來才發現,母親是在生父親的氣。“這就是對話之艱難的原因,我們常只會聽到想聽的、或是預設這個人會講出來的話。”黃惠偵說。
這一場餐桌對話一共拍了三個多小時,直到黃惠偵情緒崩潰,攝像機沒電。那天晚上,她在拍攝札記寫下感想:所謂秘密,守著難,說出口更難。
從1998年到2016年,一共18年的拍攝全部完結,黃惠偵還是沒有問出“你到底愛不愛我”這個問題。但后期剪輯的同事對她說,“你為什么還覺得媽媽不愛你,不愛你的話,誰陪你干坐那么長時間!”
04 遲來的和解
看過電影后,黃惠偵年幼的女兒在日記本里畫了兩頁畫,第一頁是《日常對話》的海報,也就是母女二人對坐的畫面;翻過來第二頁,原本坐著的兩個人站了起來,女兒在畫的下面寫著:“日常對話”站起來,結束了。
對于黃惠偵來說,承載著重大意義的《日常對話》,結束了。
2017年4月14日,電影在臺灣首映,黃惠偵把放映廳正中間的位置留給了母親,讓她無法輕易中途離場。“那大概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用挺有美感的方式來觀看自己的生命。”
看完回到家,母親徑直走進廚房,洗手,做飯,煲湯給黃惠偵喝。她開始像對待女朋友那樣對女兒輕聲細語,讓黃惠偵大感“稀奇”。這樣的情景大概維持了一個月。
阿女不再回避自己的人生,她會把電影獲獎的報道,大大方方拿給外人看,還會問黃惠偵拿票,說要帶朋友一起去看。而阿女的女朋友們,看完電影最在乎的是,“為什么那個阿姨的篇幅比我多,是不是她比較敢講?”
同樣用食物來表達愛的還有母親的兄弟姐妹們。他們看完電影后的第一個反應,是給黃惠偵帶了很多很多的食物,比如,廟里祭祀過的糖果、餅干。
“我們的上一代,不知道該如何用更好的方式表達愛和關心,他們只懂用一種方式,就是他們小時候匱乏什么,現在就會想辦法給予孩子,所以食物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表達工具。”黃惠偵說。
母親現在依然與黃惠偵租住在一起,但已經不再是《日常對話》開頭的那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跟我媽現在已經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黃惠偵說,“至少我們中間沒有隔閡,相處起來是自在的,有什么話都可以講,我覺得這就已經是很好了。”她想著,等做完眼前一個新的紀錄片工作,就搬去鄉下住,讓母親有地方可以種菜。
那句始終沒有問出口的話,在現實中已經得到了答案。
十點人物志原創內容 轉載請聯系后臺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