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網絡出現了鋪天蓋地的“以愛之名,紀念三毛逝世三十周年”特別活動報道。通曉12國語言,游歷了幾十個國家的三毛,是至今少數仍被追捧、被懷念的天才名作家。可是,大家是否知道,這位天才作家,寫作之路居然是從逃學開始,她曾經是一個“沒路可走”的自閉癥少女。那么,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三毛的寫作人生,是如何從逃學少女逆襲成天才作家的。

逃學讀書,19歲三毛發表第一篇文章《惑》
還不到三歲的三毛跑進家中的“圖書館”,打開了人生的第一本書——張樂平的漫畫《三毛流浪記》。她,找到了這一追隨終生的符號代碼:“三毛”。
三毛原名叫陳懋平。三歲的三毛,已經會認字,不愿書寫筆畫繁多的“懋”字,將其從名字中抹掉,堅持改名陳平。她家人非常尊重她,也沒說什么。
漸漸地,家里的雜志和報紙滿足不了三毛的求知欲,于是她又跑到堂二哥的書堆去“淘金”,無意中她接觸了魯迅、巴金、老舍、周作人、郁達夫、冰心的作品,她似懂非懂地讀完了全部書,開始感悟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后來大堂哥說這些書是“禁書”,全部燒掉了。
從此,三毛開始了租書生涯。那時,家里經濟狀況不好,但她依然沒放棄讀書。有毅力的三毛,總能在家里的每個角落,每件衣服口袋找到錢去租書。書店老板很好,經常推薦適合三毛和她姐姐閱讀的海外譯作、文學名著等。對名著愛不釋手的三毛,上五年級,她甚至在課堂上,把《紅樓夢》藏在裙子下面看。
三毛稱自己讀書的方式是“吞”,畢竟只有在更深更廣闊的世界里才能獲得滿足感。
初中的暑假,因為搬家,三毛又意外的發現了父親的“寶藏”,一套套線裝本的精美的俗套小說。三毛欣喜萬分,租書不間斷,現在又多了父親的這份“精神食糧”,她如獲至寶。于是,她連坐公車,都挨著車里的柱子旁若無人地讀書。
盡管初中的三毛瘋狂愛讀書,可是她在學校有四門功課跟不上。為了應付考試,她開始發奮,廢寢忘餐背下數學課后題,意外的數學取得滿分。可是,數學老師卻污蔑她作弊,并當全班同學的面,在她臉蛋用墨水畫滿了鴨蛋。
三毛不能接受來自老師同學的羞辱,她開始長期頻繁地逃課。她若無其事準時上學放學,人卻出現在沉靜的墓地中讀書,常人認知中恐怖的場所卻成了三毛的天堂。
離經叛道的三毛越走越遠,成了異類,有說她是自閉癥。初二時,她父親無奈下讓她正式退學,在家里練習寫作、繪畫。寬厚仁愛的父親又專門為她定做了一個五層的書櫥,讓少女三毛成了十足的書奴。三毛19歲時,處女作《域》,經顧福生老師推薦,發表于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雜志第五期,署名陳平。
自從《惑》在《現代文學》上發表后,三毛就從她的自閉世界走了出來,從此踏上寫作之路。

情定撒哈拉,33歲三毛出版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
1973年,30歲的三毛重遇在西班牙求學期間認識的荷西,兩人結婚并定居撒哈拉沙漠。
然而,撒哈拉沙漠條件艱苦,荷西的工資也非常低,不夠家用。深愛著三毛的父母經常從臺北給他們寄日用品,可是鄰居總是來“借用”,有借無還。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經濟越加拮據。
為了賺取稿費幫補家用,三毛應臺灣《聯合報.副刊》邀約,重新拿起筆,以“三毛”為筆名,在該報刊連載記錄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文章,廣受關注。《中國飯店》、《沙漠觀浴記》、《素人漁夫》、《娃娃新娘》、以及《荒山之夜》等文章就是在那時候寫出來的。
1976年,在撒哈拉生活的這些有趣文章,均被收錄在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里。作品一經問世,立即紅遍中國大江南北。從此,三毛的異域風情成為人們競相追捧和模仿的對象。
在《撒哈拉的故事》里,三毛將婚后生活描述得趣味橫生,她揚揚自得地敘說如何成為沙漠里的赤腳郎中,怎樣開起中國飯店、免費女子學堂,也不無遺憾地談起沙侖的愚蠢愛情,感慨著當地令人唏噓的傳統婚姻和習俗,她還介紹了如何在茫茫沙海里安下自己的小家,如何歷經艱難得到了沙漠駕駛執照等等。
接著,《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駱駝》、《橄欖樹》、《一條星光大道》等文集接連出版,三毛拿到了豐厚的稿酬,兩人的撒哈拉生活終于有了起色,偶爾還能出去旅游享受生活。《橄欖樹》后來還被選為電影《歡顏》的主題曲,家喻戶曉。不僅如此,她還與荷西一起翻譯了西班牙漫畫《娃娃看天下》。
撒哈拉沙漠生活時期的三毛,文字風格與以前截然不同,字里行間洋溢著熱情奔放與豪邁灑脫。艱苦的環境,卻活得如此鮮活,三毛的文字深深感染了廣大讀者,受到大陸及臺灣文藝青年的狂熱追捧,一度掀起了“三毛熱”。
可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1979年,荷西在潛水中意外喪生。三毛失去了一生摯愛,世界轟然倒塌,從此告別撒哈拉沙漠,回到了臺北,她的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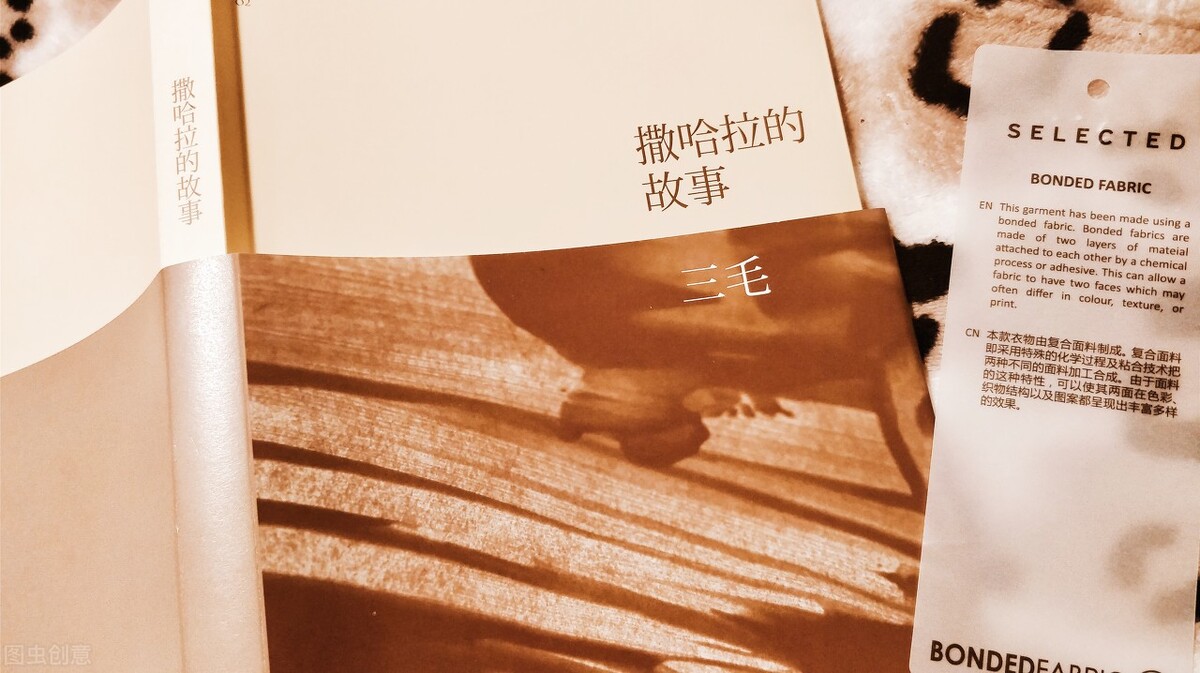
回歸臺北,最后10年人生,三毛走上寫作巔峰
回到臺北的三毛一心寫作。寫作,成為了她縫補自己那顆破碎之心的唯一方法。她把痛苦留給自己,再把感動送給世界。三毛,依然光彩奪目。
1981年,在《聯合報》的特別贊助下,38歲的三毛帶著攝影師米夏,開始為期半年多的終南美洲之旅。她們走過墨西哥、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智利等國家,回臺后多次進行公開演講,后寫成《萬水千山走遍》并出版。一夜之間,三毛聲名鵲起。
1986年,43歲的三毛被臺灣多份報刊評為最受讀者喜愛的作家。1987年,三毛出版有聲書《三毛說書》及《流星雨》。1988年,三毛聯系上了“三毛之父”,《三毛流浪記》作者張樂平,并于1989年回大陸探親時,專門拜訪了張樂平先生,并稱其為“爸爸”,一帶夙愿,了卻童年遺憾。
1989年9月,46歲的三毛在樓梯跌下摔傷,三根肋骨摔斷,斷骨插入肺里。養傷期間,她不顧傷情,在病床上為林青霞創作劇本《滾滾紅塵》。1990年12月,電影《滾滾紅塵》入圍臺灣金馬獎。
三毛從逃學少女一躍成為天才作家,受大眾追捧,可是背后她的傷痛與付出又有誰能真正懂?
回歸臺北后,三毛在家瘋狂寫作。她謝絕任何來訪,不接電話,不看報紙,甚至吃飯睡覺都成了可有可無的事。她母親心疼寫道:“我現在恨不得講出來,她根本是個‘紙人’。紙人不講話,紙人不睡覺,紙人食不知味,紙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見她的媽媽。”
父親對此亦有看法:“女兒寫作時,非常投入,每一次進入情況,人便陷入‘出神狀態’,不睡不講話絕對六親不認——她根本不認得了。但她必須大量喝水,這件事她知道。有一次,坐在地上沒有靠背的墊子上寫,七天七夜沒有躺下來過,寫完倒下不動,說:‘送醫院。’那一回,她眼角流出淚水,嘿嘿地笑,這才問母親:‘今天幾號?’那些文章在別人看來不起眼,而她投入生命的目的只為了——好玩。”
一段時間,三毛同時寫三本書,還著手翻譯12萬字的《剎那時光》。另外,又答應滾石唱片公司,寫一整張唱片的歌詞。那時剛好碰上母親患癌住院,她思想壓力非常大。一次,在探望完母親走出醫院后,她竟忘記家在何處。
三毛曾說,寫作是她生活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它不過是蛋糕上的櫻桃。此時,櫻桃已經比蛋糕重要得多。
可是,生命到了燃盡的地步,追求與自我都顯得失去意義。三毛與之而來的疾病、失眠、困頓、失落、受挫,讓她覺得活著成為一件負擔累累的事,即便生命這本秘籍沒有寫完,卻再也不知道未來該要怎樣才能進行下去。這樣活著,于三毛而言,已經與死無異。
1991年1月4日,48歲的三毛在醫院過世。

寫在最后
斯人已去多年,但她從未走出讀者的記憶。今天,我們依然懷念三毛。
賈平凹哭三毛:三毛是死了,不死的是她的書,是她的魅力。她以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創造著一個強刺激的三毛,她的死更豐富著一個使人永遠不能忘記的作家。
作家司馬中原評價三毛:讀三毛的作品,發現一個由生命所創造的世界,像開在荒漠里的繁花,她把生命高高舉在塵俗之上,這是需要靈明的智慧和極大的勇氣的。
在眾多優秀的作家中,三毛淡泊名利,卻在寫作上獲得巨大成功。三毛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奇女子。她一直以“我”在中心,將她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以及價值觀,一一展現給蕓蕓眾生。
其次,三毛的好,一半在文字,一半在她獨特壯闊的生活方式。她的筆下是一座人情溫暖的花園,是一個充滿了人情味的人間。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人生,她只是在用真情、真性感受生活;用真善、真美看待人性。真,就是她追求的平凡。另一方面,在人們眼中,三毛既是作家,也是旅行家,是夢想家更是實踐家。她靠一個灑脫的靈魂,實現了對生命的追問。她的旅行沒有目的,不是形式,而是一種探索的過程,她讓自己的生命變得無悔,變得厚重。
最后,三毛的作品處處洋溢著濃濃的愛國之情,盡管她長期漂泊海外,但她從未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在《親不親,故鄉人》中,她字里行間流露著愛國之情:”我流的不是其他民族的血液,我所關心的仍是自己的同胞和國家。在國內,也許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肩而過彼此一點感覺也沒有,可是,當我們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時,請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人。”
這就是13歲退學,19歲發表第一篇處女文章,33歲出版第一部作品的天才作家三毛;
這就是用一生書寫和傳遞愛與善的愛國同胞三毛;
這就是一個充盈著人道情懷,感動你我的作家三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