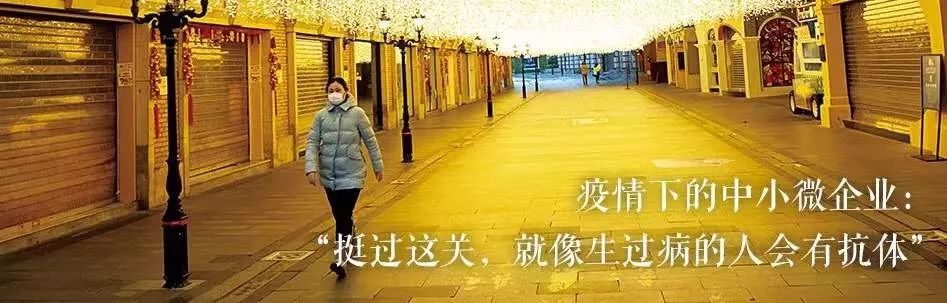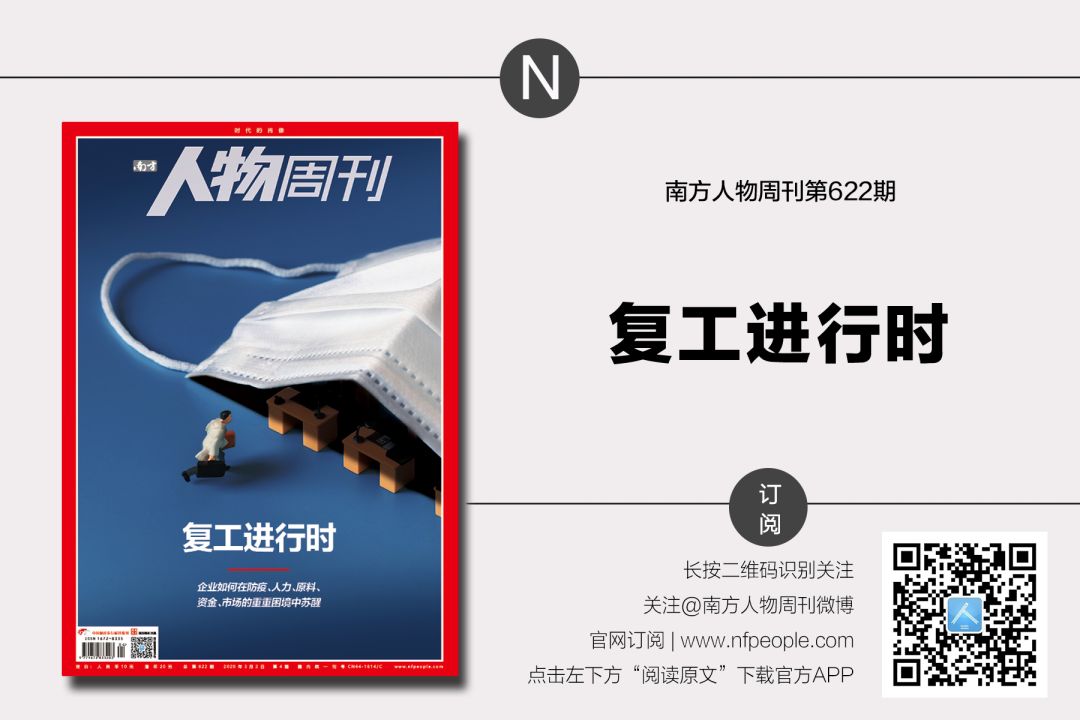2020年2月9日,武漢,一名醫護人員正在穿防護服。現階段,醫護人員的心理問題尚未浮現,他們面對的最大問題仍是超負荷工作。(拾城賴鑫琳/圖)全文共6395字,閱讀大約需要14分鐘。“真正了解的人是不忍心去碰的,就好像刀子剛剛插進去,你是不能

2020年2月9日,武漢,一名醫護人員正在穿防護服。現階段,醫護人員的心理問題尚未浮現,他們面對的最大問題仍是超負荷工作。(拾城 賴鑫琳/圖)
全文共6395字,閱讀大約需要14分鐘。
本文首發于南方周末 未經授權 不得轉載
文 |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實習生 杜嘉禧
責任編輯 | 邢人儼
過去一個月,武漢人的聲音夾雜著嘆息、消沉、焦慮和恐慌。他們的求助電話打向四面八方。至少十條熱線、數千位咨詢師為他們提供心理援助。
最多的一天,王靜接了37個電話。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能從聲音中判斷對方的內心處境。在一個女孩急切的哭泣中,王靜聽到對方已在山西老家確診,而留在武漢的男友發燒39度,仍一次次往返于協和醫院與家之間等待檢查機會。他們居住的萬松園,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并不遠,到協和醫院也只有半站路。那幾天武漢陰雨綿綿,王靜聽到了那個男孩的焦慮與絕望。
有時,一些聲音是麻木的。社區咨詢師潘蘭接過很多這樣的電話,起初很平靜,但當咨詢師開始說話,他們會急切地打斷——“你先聽我說”,說著說著就哭了——能夠哭出來,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已是幸事,“哭是一種釋放”。
在一間為火神山施工人員提供服務的酒店里,一位中年女服務員留守下來。她沒有回鄉和家人團聚,幾天后,她發燒咳嗽、頭昏無力,成了疑似患者。她排不上核酸檢測和床位,獨自在出租屋里隔離。夜里,王靜接到了她的電話,那是一個“虛弱、孤單、非常絕望”的聲音。
王靜答應,每天用私人號碼打給她,查看她的情況——她稱之為“生死約定”。這種一次性的心理援助以十到二十分鐘居多,私下聯系很罕見。連續通話一周后,對方漸漸退燒、好轉,能自己出門買藥吃飯了。
武漢人喜歡說“煩死人了”。學者易中天曾寫道,這是武漢人的口頭禪,不管要表達真正的不滿還是高興的嗔怪,他們總是嘀咕煩。
但在封城的一個多月里,留守的九百萬武漢人表現出了極大的克制。生長于此的心理醫生盧林說,武漢的市井文化靈活、樂天、包容,雖然大家很憤怒也很哀傷,但仍沒有添亂,“我們的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
一位武漢當地電視臺的年輕記者每天都要跑醫院,經常處在“崩潰邊緣”。他曾看見一位護士因病人沒救過來,在病房里放聲大哭。“這個城市每天都是生離死別。”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06年的一項研究曾指出,SARS期間被隔離者中,29%的人表現出創傷后應激障礙,31%的人有抑郁癥狀。臺灣地區的一項調查則指出,經歷SARS后,約9.2%的人對生活持有更悲觀的看法,精神病的患病率為11.7%。
作家方方接受中新社采訪時說,生活在武漢的人幾乎人人心里都有創傷,她自己也打算尋求心理幫助。未來武漢解封時,必定幾家歡喜幾家愁——人們終于自由了。“但那些病亡家屬,必然格外悲傷,燈火萬家,獨少一人。這種家破人亡的痛感只有自己知道。”
第一位上報疫情的張繼先醫生哭了無數次,病人死了、物資沒了、體力透支了,“把一生的眼淚流光了”。
洪山區心理志愿者鄢群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是從身邊人離世開始的。她發現中國人慣于逃避生死,大都沒有準備。“我想武漢市現在大多數人都體驗到了,眼淚都哭干了;沒有那么多的眼淚,因為你還要去生活。”
鄢群對南方周末記者描述武漢人的內心創痛:“真正了解的人是不忍心去碰的,就好像刀子剛剛插進去,你是不能斷然把刀子馬上抽出來的。”

2020年2月17日,武漢體育中心方艙醫院。(新華社 肖藝九/圖)
1
“每天就在等,等什么時候發作”
封城的消息公布時,大多數武漢人還在沉睡。1月23日凌晨四點,電影導演王啟明醒得早,他事后記錄下當時的感受:身體越來越沉,呼吸變得急促,“心里最后的那道防線完全垮掉了”。他叫醒愛人,對方迷迷糊糊地問:這是你做的夢嗎?
肖勁松所在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提早三周就流傳開,出現了一種和SARS類似的傳染病,甚至更狡猾。肖是神經內科醫生,他接到的第一個求助電話來自醫院內部同事,對方感染后,感到孤立無援。那時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么,也根本想不到,很快他們將見到幾十、上百位醫護人員接連感染,“都是我們的同事,一個一個地倒下”。
23歲的女孩張梓銓陪母親去醫院,發熱門診早已人滿為患,母親咳嗽發燒,但不肯做CT檢查,堅信自己“不會那么容易中招”。
封城之后不久,父親也開始咳嗽。張梓銓最好的朋友是定點醫院護士,父母也接連感染。這種被包圍的感覺,讓兩個年輕女孩覺得,“每天就在等,等什么時候發作,發作以后是嚴重還是不嚴重,你不知道哪一天會死掉”。
她堅決不肯去爺爺家過年,給爺爺打電話:我肯定被感染了,不要傳染給你們。母親怪她,“大過年的,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爺爺說:“不要緊的,你別哭。”爺爺跟著哭了起來。
23日當天,湖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開通了最早的免費心理熱線。會長肖勁松說,頭三天,每天都有一百多個來電,接近六成是不知所措的普通人。“所有外出通道都關閉了,地鐵、公交、輪渡都停運了,大家感覺有一種災難,好像大禍臨頭,好像生死存亡的時刻到了。”為熱線服務的心理咨詢師王靜說。
有人感到被拋棄,有人打算離婚,有人得了其它病不知該去哪里看,有些重疾病人沒有了藥。肖勁松的心理病人也面臨藥物短缺,他建議一位抑郁癥患者減半藥量,用7天的藥撐滿14天,不夠就再減半,吃28天,“這樣你這一個月就可以挺過去”。
社區工作者同樣感到恐懼,一位基層人員給潘蘭打電話:我其實特別擔心,家里有老人小孩,我每天在一線工作,會不會把病毒帶回去?
最初那些天,武漢一直陰雨。由于機動車禁行,李想和高燒不退的父親騎著兩輛自行車,從一家醫院跑到另一家,穿梭在排隊的、哭鬧的、喊著“快不行了”的人群里。一個中年女人無法入院,家屬甚至帶來一張床,擱在繳費臺旁邊,讓她睡下。
盧林原以為封城只會持續七天,到了初六,確診數字仍在增加。這是武漢人最為艱難的一段時間,最大的無助歸根結底還是沒有床位。即使是心理熱線,接到的大多數求助也是現實訴求。心理師們想盡一切辦法,不論公私關系,找尋床位。“這時候一張床就是一條命。”盧林說。
在持續高燒中排了12天,李想的父親才等到這張床。這期間,父親獨自在臥室隔離,門口擺著一張凳子,飯好了就擺上去,人走開了才拿。但86歲的奶奶不聽勸,總是半夜爬起來,去父親的房間摸他的額頭,看他有沒有退燒。父親住進醫院的第二天,奶奶也發燒了。
張夢琳整晚整晚睡不著,總是哭。她為母親找床位,給醫院、社區、志愿者打電話,發微博,填報了所有求助登記,得到的結果都是等通知。盡管現在已經恢復了平靜,張夢琳對南方周末記者形容當時的感受:“前面沒有任何路可以走了,就是一條死路,也沒有人可以幫你。”
為了幫一位患者尋找床位,王靜打給各級政府,聯系了所有渠道,依然解決不了。她相信如果有多余床位,一定會安排,“他們也確實無能為力”。但她不知道該怎么回撥這個電話,她不能面對——“面對一個具體的人,而這個災難發生他的身上”。
2
“哀傷是我們的權利”
即便在武漢,感染者和非感染者也仿佛置身兩個世界。母親高燒、咳血,張梓銓求助無門,同在武漢的大學輔導員打來電話,“難道你們沒去定點醫院檢查?”“定點醫院?”她感到不可思議,“你知道多厲害的人才能去嗎?”
在一個雨夜,張梓銓的父母再次趕往醫院,她看見那兩個穿雨衣奔跑的背影,歇斯底里地崩潰了。她哭到嗓子啞,想到了死亡。她打了無數電話求醫問診,一度撥通了心理熱線,不過無人接聽。
父母趕在零點前回到家,CT結果顯示母親確診。那一刻,張梓銓竟感覺“放下心來了”——“突然就覺得平靜了,真的是平靜了”。
未知和不確定幾乎把她逼瘋,現在好歹確定了。一家人商量,既然已經待在一起那么多天,之后索性不再隔離了,在家不戴口罩,也沒有消毒。
醫護人員的情緒也陷入了異樣的平靜。最初,肖勁松每天都會接到四五個醫生的求助電話,隨著疫情加重,反而變少了。他分析,大家要么處在“應激抵抗期”,來不及收拾情緒;要么就是選擇了默默忍受。他給同事們設定“硬杠桿”——當工作效率下降或不能正常生活,一定要給他打電話。當天,這個方法短暫地奏效了,之后又恢復了平靜。
王靜說,醫護人員最大的問題還是累,悶在防護服里一天,有些輪班后躺在地上就睡了,根本沒有說話的力氣。
一線救援人員常見的情況是出現“替代性創傷”——目擊他人遭受苦難,產生共情,把別人的創傷當作自己的創傷。肖勁松在汶川為救災人員提供過心理輔導,救援時,大家生龍活虎,結束后回到部隊,早晨起床號吹響,沒人起床,“心理出問題了”。
一位護士經歷了父母先后離世。肖勁松形容那種痛苦——“難以言狀,就像是眼睜睜看著親人死在自己懷里的感覺”。
這位護士繼續工作,維持在創傷應激反應的“抵抗期”——在這個階段,交感神經處于興奮狀態,仍然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被崇高的事業籠罩著,來不及哀傷”。如果進入下一個階段“衰竭期”,創傷體驗就會出現。
肖勁松問她是否愿意回家休息,她說,回家之后,面對那個房子、父母用過的東西,“我能干什么?我還不如上班。我在幫助病人的時候,感覺我在做點什么”。
“哀傷是我們的權利,哀傷是治愈心理創傷的一種情緒宣泄,我們要痛哭,要發泄情緒。”肖勁松說,“一定要學會把人的正常的情感,哪怕我們覺得是負面的情感表達出來,實際上它都是有意義的。”
2月6日晚,李文亮醫生搶救、離世的消息傳來,肖勁松所在的醫生同事群里鴉雀無聲,完全“靜默了”。由于氣氛太過壓抑,職工心理指導小組的成員悄悄問他:該怎么辦?肖勁松在群里說:讓我們哀痛一下,讓我們宣泄一下。
沉默是醫生的宣泄方式。“想說,但是又怕給李醫生添亂。”肖勁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醫護人員就是這樣一群人,當受到委屈的時候,大家就這樣承受著。我們是醫護工作者,你一發牢騷,就會影響一大批人。”
哀痛停留只此一晚,第二天,群里活躍如常,“談工作、談一些正能量的事”。
3
“別把他們當作病人”
尋死的念頭會在某些極端的時刻找上門。張梓銓的母親被確診后,醫院讓她回家隔離,“就感覺是讓我在家里自生自滅”。母親連續發燒九天,她不想吃藥,說想死,活著沒意思。張梓銓沒什么反應,父親也沒說話,就像對一切已經習以為常。
2003年SARS期間,臺北市和平醫院封院后,一名年近五旬的男性患者在病房浴室上吊自殺。“人在過于絕望的情況下,可能會實施自殺,也可能用一種‘及時行樂’‘最后的狂歡’來防御這種絕望感。”心理咨詢師于玲娜說。
1月30日下午,感染科主任向肖勁松求助,一位患者喊著要自殺。肖勁松穿上防護服,緊急進入病房。患者很激動,打針的時候一直掙扎,胳膊都腫了。她不知道自己患病,把父母、丈夫、六個月大的孩子全都傳染了。她覺得自己是家里的罪人,再沒有活下去的意義。
“那個滋味是很難受的,她不用開口,我們都感同身受。”肖勁松說。
她不敢和家人聯系,肖勁松就勸她聯系親戚、同學,為她找回情感支持。肖勁松改變她的自責認知,“你不是罪人,你和家人都是受害者。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是整個鳥巢翻了,我們都是這場大疫的受害者。”
但肖勁松也感嘆,被家人怪罪、埋怨的傳染者“太多了”。
由此產生的內疚感會讓人的心理創傷難以愈合。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專委會秘書長祝卓宏在汶川地震后做了三年心理援助,見過一位妻子反復回想,丈夫臨行前要摟著她親一口,她沒有同意,丈夫開車進山,被大石頭砸中死了。她長久惦記那個未能答應的親吻,“有內疚,就有自責,甚至會自傷、自殺”。
地震是突如其來的天災,疾病則緩緩侵蝕人體,一旦有親人確診,家屬可能陷入糾結,想靠近又不敢靠近。于玲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種痛苦可能是公共性、傳染性疾病特有的心理創傷,可能是挺復雜的創傷。”
一間方艙醫院的主任告訴肖勁松:“我們70%的工作都在處理心理問題。”
在另一家定點醫院里,有位老人堅持要出院,拒不配合,撕爛了護士的防護服,警察也趕來了。一位醫生上前安撫,聊天之后才得知,老人有老年癡呆的前期癥狀,認知功能已經退化。相處一段時間后,老人和護士們熟起來,逐漸有了安全感。
這位醫生問肖勁松,“我們這樣處理適合嗎?”肖勁松告訴他:病人反應好,就是適合的。
潘蘭接到來自疾控中心的求援,單獨隔離病房的患者怒吼、哭泣,喊著“不想活了”。盡管醫院里發放了應對心理問題的小冊子,但緊急情況下派不上用場,“你想一個處于情緒波動的人會去看嗎?”
潘蘭教醫生牽著患者的手,對他說:我們再挺一挺就過去了。“把他們當作一個正常人,別把他們當作病人。”潘蘭說,“這句話,比任何方法技巧都有作用。”
4
“給他一個滿意的結局,否則永遠也過不去”
疫情之下,生死忽然變得稀松平常。一位律師失去了七十多歲的父親,生前,父親被救護車拉著輾轉多家醫院,都沒有床位,到一處檢查、打針,兩天后又被拉去另一處、再打一針。“人的尊嚴蕩然無存,能夠被接過去打一針,已經是感恩戴德了。”他在與王靜的通話里哭得很傷心。
在這個特殊時期,尸體不能在殯儀館停放,當場就得火化。王靜說,這會給家人留下創傷,需要“完形治療”——等疫情過去,她建議律師帶著父親的骨灰,回老家辦一場體面的葬禮,“給他一個滿意的結局,否則永遠也過不去”。
傳統文化中的喪葬儀式原本是很好的心理療愈。“沒有追悼會、沒有很好的臨終關懷,就會很難療愈失去親人的心理創傷。”祝卓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死亡一個人,周圍的直系親屬可能得達到6-8個,最痛苦的就是這部分人,他們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創傷性哀傷,創傷后的抑郁以及自殺風險還是存在的。”
潘蘭的一位朋友向她求助——六十多歲的父親感染了,在醫院上了呼吸機。潘蘭為她紓解情緒。三天后她再打過去,對方說,父親已經走了,上次通完話,次日夜里沒挺過去。
“爸爸走的時候,我連摸都不能摸他。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磕頭。”掛掉這個電話,潘蘭痛哭了一場。
一對年輕夫妻育有十歲的龍鳳胎,丈夫感染新冠肺炎,突然去世。妻子把自己關起來,閉門不出,不接任何親友的電話。社區婦聯主任找到鄢群,向她求助。鄢群回答:她現在的自閉就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把菜送好、孩子看好,“讓她在自己的世界里待一段時間吧”。
盧林在汶川見到很多人,事發一個月后創傷才開始浮現。有人離開了四川,外出流浪;有人看透了生死,再難獲得安全感。
某種程度上,張梓銓是幸運的,母親漸漸退燒,精神也好起來了,社區安排她去酒店隔離。但這個女孩身上的一些東西已經永遠被改變了——她發現過去所知的常識全都失效了,“原來你之前的生活是那么脆弱”。
最初的幾天,她還盤算著封城結束之后可以去喜歡的電視臺實習,“還在想‘前途’這種很高等的需求”。現在,這個愛打扮、愛吃喝玩樂的女孩每天躺著,不洗頭、不洗澡,父親做點飯,她就吃一點。張梓銓覺得自己已經不是“正常人”。
托爾斯泰的一句話也許可作為參照,“把死置諸腦后的生活,和時時刻刻都意識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
因為在網上求援,有記者采訪張梓銓,問她是否需要幫助。她回答:希望你們多關心那些更底層的人——“不會上網、沒有關系、無車無房無親戚無任何保證的人,他們怎么辦呢?”
每當張梓銓在微博上表達武漢人的痛苦,就有人來和她辯論,指責她傳播恐慌。“好像打破了誰的美夢一樣。我不說的話,那些人不就白死了嗎?”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們好像不是一個病人,也不是一個人,他們就是恐慌的源頭。”
“他們都是我每天擦肩而過的人,一起排隊買奶茶的人,買菜閑拌兩句嘴的人,現在,我們、他們,都成了‘災民’,甚至成了‘死者’,成了追著殯儀車哭嚎叫喊的人,我如何去接受?”張梓銓說。
2月15日,武漢下了一場大雪,雪花覆蓋在空蕩蕩的街道與很久無人開動的汽車上。往常這樣的時候,鄢群會很高興,因為可以去梅園賞雪了。這一天她待在家里接求助熱線,擔憂著外頭值守的警察、工作人員,太冷了,“千萬不能感冒啊”。
張夢琳平復了下來,母親終于住院了。她祈求命運的方式是“行善積德”,很多志愿者給她送了藥,她打算等14天隔離結束,就去報名給老人送菜。
“他們開始懂得,死亡時刻威脅著每個人……”托爾斯泰寫道,“他們也開始懂得,疾病不應該把人們分開,恰恰相反,它應該為人類相愛提供機會。”
王靜總是描述武漢有多美,來寬慰熱線咨詢者。她邀請外地人在疫情結束后來看武大的櫻花。她對武漢人會說:讓我們春暖花開時,相約在東湖綠道,相約在黃鶴樓。
所有心理援助者都清楚,疫情終會結束,但武漢人內心的安寧不知何時到來。

戰“疫”專題: